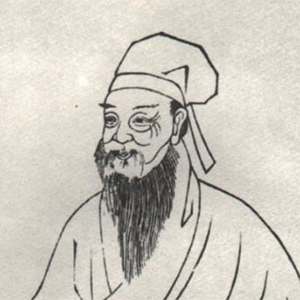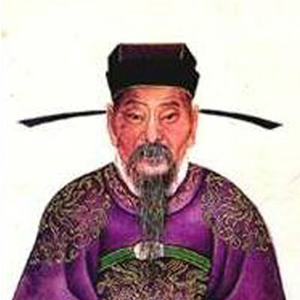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蜀中多产棕榈,十有八九都长得很高大。
棕毛虽多但割开剥下太多,树也容易枯朽。
棕榈尽管具有大如云的树叶和经岁寒而不凋谢的生命力。
但是如果过量地砍伐,它将比易衰的蒲柳更早地凋落。
当时军用物资缺乏,连棕毛也要取尽(编为马具)。
可怜你们江汉人所生产的东西还剩什么呢?
就好像割剥过甚的枯棕一样,不能不使我深深叹息。
死者也就罢了,生者又凭什么保全自己的性命呢?
见到啾啾的黄雀不停地啄着棕榈,棕毛如同飞蓬一样乱飘。
不禁想到如此高大的乔木也被摧残得形影枯于,埋没在杂草中了。
注释
蜀门:犹蜀中,即成都。
棕榈:也作“椶榈”,常绿乔木,棕榈皮上有毛,称棕毛,可制绳帚刷等,故下有“割剥”语。
十八九:十有八九。
割剥:割开剥下。
如云割:如云样的棕割,形容棕割甚大。
岁寒后:指棕榈和松柏一样,虽经岁寒而不凋谢。
斧斤:伐木的工具。
先蒲柳:比蒲柳先凋落。蒲柳,生在水边的水杨,又称蒲杨,易生也易衰。
军乏:军用缺乏。
一物:指棕榈。
取:此处读zhǒu。
江汉人:四川人。汉,指西汉水,即嘉陵江,此处用江汉代指蜀中、蜀门、巴蜀。
生成:指上文以“棕榈”为代表的地之所生、人力所成的“物”。
复何有:还有什么。
啾啾:虫、鸟细碎的叫声。
啅:鸟雀叫声,一作啄。
蓬:草名,又叫飞蓬。
形影干:形容棕榈枯干,一作枯形影。
没:埋没。
藜莠:恶草的通称。
这首诗创作于上元二年(761)秋,当时中原战乱未平,蜀中又有藩镇割据之患(如不久前的段子璋之乱),加上西面吐蕃屡相侵扰,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集。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军兴而赋重的局面,下层百姓被重赋盘剥而欲活不得的悲惨处境,不能不引起杜甫的深切关注与同情,遂借物言情,托棕榈之被割剥过甚以至于枯死,来寓蜀中百姓的惨遭暴敛而生存无路。作者由棕之枯,看出了剥削的残酷和人民的痛苦,于是写了这首诗。
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这首词写于作者中年以后溯江而上之时。他有志报国,投书献策,希图仕进,并劝说诸路帅臣,致力恢复中原,均未奏效,流寓他乡,抑郁不平。上片写依人客居,抒寻秋思乡的失意之情。起首三句先用冯谖弹铗的故事叙说自己从金陵西上,旅途艰苦、窘迫十分不得意的状况。“梦里”三句点明时间是在秋季,心情的苦闷,更勾起思乡的情怀。但家乡路遥。欲归不得,更令人伤感。“万里”以下,感叹自己长期在外奔波,岁月流逝,年纪已老,却事业无成,字句之间,流露出深沉的感慨。下片追忆青年时代的凌云理想与豪迈气概,抒请缨无路的惆怅。那时他的理想虽无人理解,但他自己立下不澄清中原绝不罢休的壮志,酣放自若,不可一世,连腰上的宝剑也发出声来表示要上阵杀敌,可现在他竞一事无成,谁能理解他此时的心绪?最后他希望有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人,用他们的诗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情绪。
本词抒发了作者事业无成的忧虑和苦闷,写来如水银泻地,挥洒无余。风格豪放,感情深沉,用典贴切,笔力峭拔。刘熙载《艺概》中称刘过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读者可从这首词中不难看出。
两千多年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不知感动过多少中国人的心灵。在吟咏牛郎织女的佳作中,范成大的这首《鹊桥仙》别具匠心是一首有特殊意义的佳作。
“双星良夜,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起笔三句点明七夕,并以侧笔渲染。“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岁华纪丽》卷三“七夕”引《风俗通》),与牛郎相会,故又称双星节。此时银河两岸,牛郎已无心耕种,织女亦无心纺绩,就连天上的众仙女也忌妒了。起笔透过对主角与配角心情之描写,烘托出一年一度的七夕氛围,扣人心弦。下韵三句,承群仙之相妒写出,笔墨从牛女宕开,笔意隽永。“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形貌娟秀的嫦娥蹙紧了蛾眉,风姨竟然兴风吹雨骚骚然(风姨为青年女性风神,见《博异》)。这些仙女,都妒忌着织女呢。织女一年才得一会,有何可妒?则嫦娥悔恨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可知,风姨之风流善妒亦可知,仙界女性之凡心难耐寂寞又可知,而牛郎织女爱情之难能可贵更可知。不仅如此。有众仙女之妒这一喜剧式情节,虽然引出他们悲剧性爱情。词情营造,匠心独运。
“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下片,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相会情景一笔带过,更不写“忍顾鹊桥归路”的泪别场面,而是一步到位着力刻画牛郎织女的心态。七夕相会,匆匆而已,如此一面,怎能错见!见了又只是重新撩乱万千离愁别绪罢了。词人运笔处处不凡,但其所写,是将神话性质进一步人间化。显然,只有深味人间别久之悲人,才能对牛郎织女心态,作如此同情之理解。“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结笔三句紧承上句意脉,再进一层刻画。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之别离,相逢仅只七夕之一刻,旧愁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深重,新欢又何其有限。不仅如此。旧愁未销,反载了难以负荷的新恨归去。年年岁岁,七夕似乎相同。可谁知道,岁岁年年,其情其实不同。在人们心目中,牛郎织女似乎总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已。
然而从词人心灵之体会,则牛郎织女的悲愤,乃是无限生长的,牛郎织女之悲剧,乃是一部生生不灭的悲剧,是一部亘古不改的悲剧。牛郎织女悲剧的这一深刻层面,这一可怕性质,终于在词中告诉人们。显然,词中牛郎织女之悲剧,有其真实的人间生活依据,即恩爱夫妻被迫长期分居。此可断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曲词)
此词在艺术造诣上很有特色。词中托出牛郎织女爱情悲剧之生生不已,实为匪夷所思。以嫦娥风姨之相妒情节,反衬、凸出、深化牛郎织女之爱情悲剧,则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黑色幽默庶几近之)全词辞无丽藻,语不惊人,正所谓绚烂于归平淡。范成大之诗,如其著名的田园诗,颇具泥土气息,从这里可以印证之。最后,应略说此词在同一题材的宋词发展中之特殊意义。宋词描写牛郎织女故事。多用《鹊桥仙》之词牌,不失“唐词多缘题”(《花庵词选》)之古意。其中佼佼者,前有欧阳修,中有秦少游,后有范成大。欧词主旨在“多应天意不教长”,秦词主旨在“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成大此词则旨在“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可见,欧词所写,本是人之常情。秦词所写,乃“破格之谈”(《草堂诗馀隽》),是对欧词的翻新、异化,亦可说是指出向上一路。而成大此词则是对欧词的复归、深化。牛郎织女的爱情,纵然有不在朝暮之高致,但人心总是人心,无限漫长之别离,生生无已之悲剧,决非人心所能堪受,亦比高致来得更为广大。故成大此词,也是对秦词的补充与发展。从揭橥悲剧深层的美学意义上说,还是是对秦词之一计算。欧、秦、范三家《鹊桥仙》词,呈现一否定之否定路向,显示了宋代词人对传统对人生之深切体味,亦体现出宋代词人艺术创造上不甘逐随他人独创精神,当称作宋代词史上富于启示性之一佳话。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这两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开头两句,描绘送别时候的自然景色。黄云蔽天,绵延千里,日色只剩下一点余光。夜幕降临以后,又刮起了北风,大风呼啸。伴随着纷纷扫扬的雪花。一群征雁疾速地从空中掠过,往南方飞去。这两句所展现的境界阔远渺茫,是典型的北国雪天风光。“千里”,有的本子作“十里”,虽是一字之差,境界却相差甚远。北方的冬天,绿色植物凋零殆尽,残枝朽干已不足以遮目,所以视界很广,可目极千里。说“黄云”,亦极典型。那是阴云凝聚之状,是阴天天气,有了这两个字,下文的“白日曛”、“北风”,“雪纷纷”,便有了着落。如此理解,开头两句便见出作者并非轻率落笔,而是在经过了苦心酝酿之后,才自然流一出的诗歌语言。这两句,描写景物虽然比较客观,但也处处显示着送别的情调,以及诗人的气质心胸。日暮天寒,本来就容易引发人们的愁苦心绪,而眼下,诗人正在送别董大,其执手依恋之态,我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首二句尽管境界阔远渺茫,其实不无凄苦寒凉;但是,高适毕竟具有恢弘的气度,超然的禀赋,他并没有沉溺在离别的感伤之中不能自拔。他能以理驭情,另具一副心胸,写出慷慨激昂的壮伟之音。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是对董大的劝慰。说“莫愁”,说前路有知己,说天下人人识君,以此赠别,足以鼓舞人心,激励人之心志。据说,董大曾以高妙的琴艺受知于宰相房琯,崔珏曾写诗咏叹说:“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写的不过是董大遇合一位知音,而且是官高位显,诗境未免狭小。高适这两句,不仅紧扣董大为名琴师,天下传扬的特定身份,而且把人生知己无贫贱,天涯处处有朋友的意思融注其中,诗境远比崔珏那几句阔远得多,也深厚得多。崔诗只是琴师身世的材料,而高诗却堪称艺术珍品。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