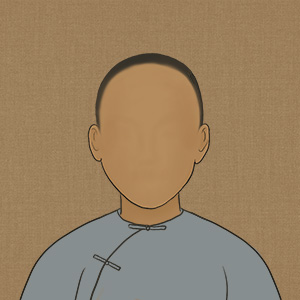此词上片从游湖写起,讴歌春色,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色彩鲜明的早春图;下片则一反上片的明艳色彩、健朗意境,言人生如梦,虚无缥缈,匆匆即逝,因而应及时行乐,反映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寻欢作乐思想。作者宋祁因词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而名扬词坛,被世人称作红杏尚书。
起首一句泛写春光明媚。第二句以拟人化手法,将水波写得生动、亲切而又富于灵性。“绿杨”句写远处杨柳如烟,一片嫩绿,虽是清晨,寒气却很轻微。“红杏”句专写杏花,以杏花的盛开衬托春意之浓。词人以拟人手法,着一“闹”字,将烂漫的大好春光描绘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过片两句,意谓浮生若梦,苦多乐少,不能吝惜金钱而轻易放弃这欢乐的瞬间。此处化用“一笑倾人城”的典故,抒写词人携妓游春时的心绪。结拍两句,写词人为使这次春游得以尽兴,要为同时冶游的朋友举杯挽留夕阳,请它在花丛间多陪伴些时候。这里,词人对于美好春光的留恋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这首词章法井然,开阖自如,言情虽缠绵而不轻薄,措词虽华美而不浮艳,将执著人生、惜时自贵、流连春光的情怀抒写得淋漓尽致,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
本词歌咏春天,洋溢着珍惜青春和热爱生活的情感。上阙写初春的风景。起句“东城渐觉风光好”,以叙述的语气缓缓写来,表面上似不经意,但“好”字已压抑不住对春天的赞美之情。
以下三句就是“风光好”的具体发挥与形象写照。首先是“縠皱波纹迎客棹”,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盈盈春水,那一条条漾动着水的波纹,仿佛是在向客人招手表示欢迎。然后又要人们随着他去观赏“绿杨”,“绿杨”句点出“客棹”来临的时光与特色。“晓寒轻”写的是春意,也是作者心头的情意。“波纹”、“绿杨”都象征着春天。但是,更能象征春天的却是春花,在此前提下,上片最后一句终于咏出了“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绝唱。如果说这一句是画面上的点睛之笔,还不如说是词人心中绽开的感情花朵。“闹”字不仅形容出红杏的众多和纷繁,而且,它把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全都点染出来了。“闹”字不仅有色,而且似乎有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下阙再从词人主观情感上对春光美好做进一步的烘托。“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二句,是从功名利禄这两个方面来衬托春天的可爱与可贵。词人身居要职,官务缠身,很少有时间或机会从春天里寻取人生的乐趣,故引以为“浮生”之“长恨”。于是,就有了宁弃“千金”而不愿放过从春光中获取短暂“一笑”的感慨。既然春天如此可贵可爱,词人禁不住“为君持酒劝斜阳”,明确提出“且向花间留晚照”的强烈主观要求。这要求是“无理”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却能够充分地表现出词人对春天的珍视,对光阴的爱惜。
这首诗的开篇,干脆利索,开门见山,一气呵成,将诗人内心愤懑苦恼的矛盾心理悉数展现在读者眼前。前八句直抒感慨,亦是对诗人前半生仕途的总结。少年气盛之时,不谙世事,尽力苦学只为求取功名利禄。行至途中,回首走过的仕途,却是那般苦不堪言。“强学”、“徒闻”、“苦无”、“闻徒言”、“累官”、“寡”、“恐遭”,这一连串如泻闸之水般喷涌而出的用词,无不流露出诗人的苦闷之情。在这开门见山的畅吐背后,不难想象出诗人仕途跋涉中的艰辛与烦恼,那苦不堪言的心情,身心俱碎的状态。然处在这样的仕途漩涡里,又是闻能奈何得了的。想要“遂性欢”,却又害怕遭来“负时累”。面对世俗纷繁的厌倦,对现实世界的进退维谷,矛盾交织的内心挣扎,低首徘徊的他,究竟又该何去何从。前八句一泻而下的倾诉,将诗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得遗漏无疑,在读者面前勾画出一位茫然徘徊,为人生追求而苦闷的仕者形象。
诗的后八句,诗人笔锋一转,转而描绘出一幅清新高渺、晶莹剔透的画面,压抑沉重的氛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焕然一新的画面,清冬的远山,清晰可见,晶莹的雪花,将苍翠的山林覆盖,天地间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几许透亮,几许静穆。如此心旷神怡之境,将尘世的繁杂与诗人内心的苦闷化为乌有,这才是他真正渴望追求的境界。“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事意。”这是此番自然景象给诗人的启迪,亦是诗人内心最深的夙愿。末两句是劝诫堂弟之语,堂弟素来追求高雅之趣,早年极言追求“尘外”之意,却仍陷世俗之中,诗人想与堂弟携手共同隐退而居,却怎奈世俗纷扰,仍有故得延缓归期,然时光却转瞬即逝,匆匆而过。末句看似对堂弟的规劝,实则也是对自己进退两难境地的慨叹,忧谗畏祸的心情溢于言表。
此诗发言旷远,用笔委婉。前后部分的巧妙转折,是一个诗人心灵与自然对话的过程,自然的开阔之境将他从苦闷之际释放出来。
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