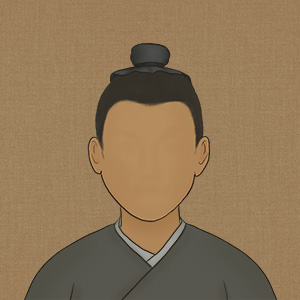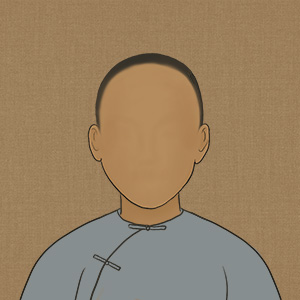京洛染缁尘,悠然意,独对南山一笑。只在此山中,甚相逢不早。瘦吟心共苦,知几度、翦灯窗小。何时更、听雨巴山,赋草池春晓。
京洛染缁尘,悠然意,独对南山一笑。只在此山中,甚相逢不早。瘦吟心共苦,知几度、翦灯窗小。何时更、听雨巴山,赋草池春晓。
这首词写的是作者闻歌伤怀之感,其情事大致类于白居易之《琵琶行》,然而小词对于长诗,在形式上有尺幅与千里之差别。
上片写歌女的演唱,相当于白诗对琵琶女演奏的叙写。“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一曲歌而能具千重意,想必亦能说尽胸中无限事;而这“无限事”又必非乐事,当是平生种种不得意之恨事。这是从后二句中“恨”“泪”等字可得而知的。首二句巧妙地运用了对仗加顶真的修辞,比较一般的“流水对”更见跌宕多姿,对于歌唱本身亦有模似效用。“才欲歌时泪已流”一句乃倒折一笔,意即“未成曲调先有情”。
“恨应更、多于泪”,又翻进一笔,突出歌中苦恨之多。白居易诗对音乐本身的高低、疾徐、滑涩、断连等等,有极为详尽的描摹形容。而此词抓住歌者形态特点层层推进,启发读者去想象那歌声的悲苦与宛转。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对歌女的悲凄身世作了暗示,相当于琵琶女放拨沉吟、自道辛酸的大段文字。但白诗中的详尽的直白,此完全作了暗示的处理。当听者为动听的演唱感染,希望进一步了解歌者身世时,她却“不语如痴醉”。这样写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末三句写词人由此产生同情并勾起自我感伤,相当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自我表白。但此词却只说“我亦情多不忍闻”,好像是说:歌女不语也罢,只怕我还受不了呢。由此可知,这里亦有一种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感情,因此以至于“怕和我、成憔悴”。
和白居易《琵琶行》不同的是,这首词善抒情,妙悬念的设置,化实为虚,得其空灵。同时,此词运笔颇饶顿挫,上片用递进写法,下片则一波三折,读来引人入胜。《卜算子》词调上下片的两个结句,本为五言句,此词则各加了一个衬字变成六言句(三三结构)。大凡词中加衬字者,语言都较通俗,此词亦然。
这首词写采莲的楚女欲归南浦与风吹波起、小船渐行渐远的情景,表现了一种淡淡的哀愁,这哀愁是楚女驾舟归去的一霎那所引起的,是岸上送者的哀愁,也是楚女的哀愁,只是送者并未出场,却从行者眼里写出。
首起二句“楚女欲归南浦,朝雨”点明人物、情事、地点、环境。紧接着“湿愁红”句,用雨湿花红烘托气氛。花红无所谓愁与不愁,但在朝雨归去的离人眼里,却带上了愁的轻纱。“小船摇漾入花里”写船行,“摇漾”二字描摹出小船轻悠地荡漾在花丛中的情态。“波起”写船行荡起层层涟漪。这里描述小船驶入花丛的情景,概括地写出了江南水乡充满诗意的美景,描绘出一种极美的境界。雨湿花红,风吹浪起,如此离别的环境气氛,愁意自在其中。
结尾“隔西风”三字,语言简洁,却深入地写出了送别女子的心情:西风吹起,碧波荡漾,人儿远去,无影无踪,倩影留在眼前,哀愁充满心田。其中一“隔”字,以硬笔写感情,给人以刚硬之感,表现出一种被强行拆散的感受。“西风”则是一种萧瑟的意象,与“朝雨”交加,更添凄凉,透露出送者与被送者的苦楚哀伤。
此词篇幅虽然短小,却能以少许断续的线条,绘成一幅饶有情趣的人物小景。一个“愁”字,一个“隔”字,写楚女悠悠离愁颇为宛转含蓄。全词“曲调节拍短促,而韵律转换频数,形式与五、七言诗大异其趣,令人一新耳目”(胡国瑞《论温庭筠词的艺术风格》)。
这是一首送别词,主要是描叙元济之的离愁别绪的。词中没有写作者同元济之间的离愁别苦,这是本词和一般送别词的不同之处,也是它的主要特点。情调幽怨,相当动人。
起句写元济之的衰老。元济之倚枕而卧,显得有些衰老。接以“两鬓霜”三宇,则其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之状可知。“起听”句写其生活无聊。谓其有时起来,走到廊下,谛听檐溜的喧嚣声,以消磨时光,排遣心中的郁闷,可见其生活的寂寞与孤苦。“那边”二句写其对家乡的思念。欲写元济之思念家乡,先写家人思念元济之。这不仅使行文委婉曲折,更加重了元济之的思乡之情。啼粉,与啼妆同意,指薄拭眉下若啼之妆。而“玉筯消啼粉”,写其家人因相思而流泪,把啼粉都冲掉了。“这碎”句,言元济之远游在外,日日思念家人,别肠如车轮旋转,无休无尽,则其思乡之甚可知。元济之如此思乡,很自然地就逗出了送别之意,从而点明了题旨。“诗酒”二句写元济之在外的生活。言其游历于山水之间,并和友人聚会饮酒,结社赋诗,徜徉于水云之乡,生活似乎极为潇洒飘逸,其实内心是很凄苦的,故接下去说“可堪醉墨几淋浪”。可堪,为不堪、哪堪之意。“醉墨淋浪”,化用欧阳修“新诗醉墨时一挥。别后寄我无辞远”,言其挥笔写诗作画,醉墨淋漓,其间着一“几”字,隐含机会不多之意。结尾二句承“醉墨”而发,借画发挥;言其“归家梦”和其所作图画一样,在画图中能把千碎河山收入“寸许长”的画幅之中,而“归家梦”也能转瞬之间实现,从而表达出立即送其“归豫章”之意。在此,以画作比,语新意丰,蕴藉含蓄,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