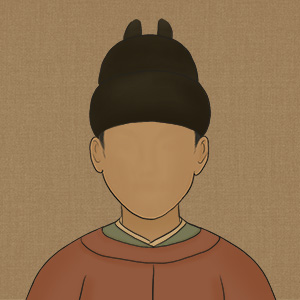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
曾国藩一生从政从军,事务庞多,但他从来不曾忘怀故园之思,手足之情。本诗即是他的念弟之作中写得较好的一首。诗的首联即直接将奔波中的感受写出,每天凌晨,在繁星点点的时候,这原本是酣眠的良辰,作者却早已整驾上路了,又疲惫又寒冷,确是苦不堪言,于是他对这种生活发生了怀疑,不禁扪心自问,如此奔忙劳碌意义究竟何在?(底,何,什么)这二旬写得感情充沛、真挚。然后诗转入写景。在孤月的清晖之下,作者看到了马的疲惫身影,内心里生出对它的怜意。马的形,实际上是作者情感的对象化;对马的怜悯,其实就是作者的对影自怜;这种心境之下的月亮,自然也显得那么孤单寂寞。接着,孤月西落了,一声报晓的鸡鸣划破黑夜,渐渐可以辨认出那深青色的群山了。万山环绕,更令作者感到道路之艰、身心之疲惫;远处鸡鸣,亦暗示了作者身处不见人烟的荒山,孤零无人语:这句写得虽具开阔气象,但一个“苍”字,仍给诗情增添了一份悲苦苍凉之意,由此,诗人对手足同胞的思念之情,也自然向高峰处涌去。这两句景语也是情语,是诗人心态的写照。
于是,颈联便唱出了。日归日归岁云暮,有弟有弟天一方”的戚苦之调。无数次的念归,可是从未真的归去,而今又到了年终岁暮,更难知何时能踏上归程;离家愈久,愈是恋家,时时思念自己的弟弟,现在,只能是天各一方,无从团圆,只能在旅途的孤独寂寞中体验兄弟的至情。二句中,上句虽化自《诗·采薇》的“日归日归,岁亦莫(暮)止”,但与下句配合,运用反复之法,亦适切地描摹出诗人此时此刻的心灵波涛,给人一唱三叹之感。最后二句,诗又回到清晨赶路的现实,他这时面对的是深深的大壑,高高的山崖,还有强劲的晨风。不用说,这样的环境再次强化了诗人的思念之情,情感的波涛再次涌起,但是诗人似乎不愿再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于是故意逃脱,自寻宽解:如此猛烈的风或许可以吹送我早些回到弟弟的身旁吧!这一笔似是荡开,似是感情的排遣,心理的安慰,但因为这番幻想事实上是不可能之事,所以诗中一直蕴含着的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无可奈何之情,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
本诗情感真挚,格调苍凉,以情绪的流动起伏贯穿全诗,思归念弟之情与诗人奔走宦路之苦的反复咏叹,更收到悠远绵长的艺术效果。因此,尽管在中国诗歌中怀人之作不可胜数,但这首念弟诗仍然显示出独有的艺术魅力。
据阮阅《诗话总龟》等书记载:“南唐卢绛病痁,梦白衣美女歌曰:‘玉京人去秋萧索’云云。”从此这首小词蒙上一层迷离恍惚的神秘色彩,被看作“鬼词”。其实,这只是一首倾诉闺情的篇章,它以笔致工巧,深婉动人,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曾在北宋初年广为流传。从词中可知,抒情主人公是一位温柔多情、敏感娴静的女子。
“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在这萧索的秋天,心上的人儿远去京城,庭院画檐下喜鹊飞起,梧桐纷纷飘落。
玉京,本道教所谓天上宫阙,用作京城的代称。在一个秋日的黄昏,她凭栏凝视,沉浸在对远方亲人的怀念之中。起首两句描绘出一幅飒飒秋景,景中有情。前一句点出秋气而“人去”之意,是情与景双双写入之法。“萧索”二字是一篇眼目,后一句就此点染。喜鹊历来是吉祥之鸟,鹊起而不顾,暗示丈夫一去杳无音信,闺中的主人公怅然失望也已隐然可见,细微如梧桐落叶之声清晰可闻,庭院之阒寂,女子怀想之深也可以想见了。“人去”,令人记起往昔未去之时;“萧索”,烘衬出抒情者的悲凉意绪,连带说出便觉情景相生,这正是双入法的妙处,由此开篇,全词都笼罩着瑟瑟寒意了。基调也由此确定。
“攲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这两句是说,倚靠着枕儿默然远想,月儿和梦境都是那么的圆美。
接下来时间由黄昏而入夜。如果说前面两句侧重渲染气氛的话,那么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的动作。中心落在思念二字上。夜不安寐,倚枕无言,用动作表现心理,形象而又委曲。“无言”是静默之状,又含“脉脉此情谁诉”之意。唯其默然远想,才引出下一句的清梦来。不知过了多久,这位辗转反侧的女子渐渐进入梦乡。梦中见到了她久别的亲人。词人把这梦中团聚和中天月圆巧妙的交织在一句之中,“圆”字双关。梦境沐浴着月的清辉,而一轮圆月又在梦的幻影之中,境界惝恍迷离,清幽怡人。梦境与现实,月色与人事两相对照反衬,使主人公的情怀表现得愈婉愈深了。
“背灯唯暗泣,甚处砧声急。”这两句是倒装句,说,不知什么地方响起阵阵捣衣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眼前的冷寂,益发加深了感伤和怅惘,她怎能不柔肠寸断,哀泣不止呢?
“甚处”,说明砧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是一种并不太响,而且时断时续的声音,也符合乍醒来时恍惚莫辨的情态。这种声响竟把人惊醒,可知夜之静谧了。这样看来,句中极醒目的“急”字恐怕侧重于表现人的内心感受,未必是实写砧声。“背灯暗泣”乃梦断神伤之状。“暗”字兼言情、景,思妇心境之黯然具体可感。从上文的“攲枕悄无言”到此刻的“背灯暗泣”,层层叠进,愈转愈悲了。
“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结末两句是说,室内女子黛色如远山的眉头紧攒,室外圆月清辉之下芭蕉也觉瑟瑟寒意。
给那攒蹙的秀眉一个特写镜头,把满怀的思念和哀怨全部凝聚在黛色如远山的眉间了。末句轻轻宕开,以景收束:“芭蕉生暮寒”。凄冷之意有真切,又朦胧,那寒气直沁入人的心里,却又不曾说破。词婉而情切,令人哀感无端,正是所谓已经结情的妙笔。
这首词在结构上,一句景,一句情,间或情景双写。在情与景的相映、相生、相融之中,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婉曲而深切的袒露出来了。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