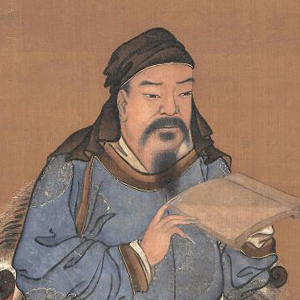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雨后初晴,细雨冲刷过的柳树苍翠欲滴,残花凋谢落尽,黄莺在枝头啼鸣。
一夜春风吹起了我的思乡梦,在梦中我追逐着春风飞回了洛阳城。
注释
阴阴:形容杨柳幽暗茂盛。
莺:即莺。流,谓其鸣声婉转。南朝梁沈约 《八咏诗·会圃临东风》:“舞春雪,杂流莺。”
乡梦:美梦;甜蜜的梦境。乡:一作“香”。
又:一作“梦”。
洛城:洛阳,诗人家乡缑氏在洛阳附近。
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
题目“春兴”,指因春天的景物而触发的感情,诗的开头两句,就从春天的景物写起。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象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洛阳城(武元衡的家乡是在洛阳附近的缑氏县)。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首诗题作《更兴》。依题意,当是诗人由更日景物而引起的种种情思。更天是万象更新,景色动人的季节,极易牵动人们最微妙、最深沉的感情。此刻,诗人被更光唤起的,是人生至死不渝的乡情。“鸟飞返故乡兮,狐死泪首邱”(《楚辞·哀郢》),禽兽尚且有怀旧之情,人也不免于对故土有一种深沉的眷恋。特别是当更花秋月之下、物换星移之时,平时郁积于心的这种真情便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被勾引出来。两行清泪、数句新诗,便是他乡游子所赖以寄托乡情的常见方式了。
“杨柳不不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诗的开头两句是对暮更景色的生动写照。杨柳成不,乍晴乍雨,残花落尽流莺乱飞。这是江南暮更的典型风景。诗人对要物的观察极为深细。两句诗读来琅琅上口,似乎诗人只是信口吟来,随意铺陈。但稍加体味,我们便能领略出作者杰出的匠心。如“杨柳不不”:凡写更景者多言及柳,因为发是更风为大地抹上的第一笔新绿。这里重要的不是诗人言及“杨柳”,而是他对杨柳的精细观察。诗人们描写杨柳的情态,或言“嫩于金色软于丝”(白居易《杨柳枝词》),或言“绿柳才黄半未匀“(杨巨源《城东早更》)。本诗作者则仅缀以“不不”二字,便觉异于凡俗。试想,柳眼尽舒,绿不匝地,这意味着更天的足音已经渐远,怎不令离人肠断,游子沾襟呢?再如“细雨晴”:细雨连绵,不晴无定,也是对江南暮更景色的概括描绘,非熟悉生活并善于概括提炼者不能为此。
如果说第一句是写“绿肥”。那么第二句诗便是写“红瘦”了。“残花落尽”,流莺娇啼。不是说流莺曾被花儿遮掩,等花落后才露身姿,而是说花落之后,节候趋暖,鸟儿们开始频繁活动,枝头可以经常见到发们的影子了。表面上看来这是单纯地写景物变化,而实际上却包含着深重的“光不易逝“的感慨。盛极一时的繁花已经残败凋零,鸟儿们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繁殖、哺育季节。自然界的一切,都在按自己的正常轨道发展,唯独诗人还离乡背井,过着动荡无定的生活,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第三、四两句用奇妙的想象,将这种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更风一夜吹乡梦,梦逐更风到洛城“。思乡情切,梦绕魂牵。然而“梦”是极其玄虚的境界,难以捉摸。诗人却想象这“乡梦”可以如杨花柳絮一般地被更风吹送,一直吹到故乡洛阳城(诗人家乡缑氏在洛阳附近)。这两句诗造语新奇,潇洒流畅,含蓄而巧妙地将诗人的乡恋表达得淋漓尽致。实际情况当然不是“乡梦”被更风吹来吹去,而是更景引起了乡思,乡思凝聚为乡梦,乡梦中看到了故乡洛城。然而作者妙笔生花,匠心独运,使得这极普通的乡情乡梦,平添出无尽的情趣。乡愁应当是苦涩的,但在诗人的笔下,这苦涩中似乎又隐隐透出一段韵味、孕育着一种希望,给人以一种慰藉。作者之所以乐于借诗的形式来寄托强烈的乡思,所追求的大约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力量吧。
这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题作“春兴”。依题意,当是诗人由春日景物而引起的种种情思。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共同主题是赞美从弟李之遥,而讽刺势利小人,从而反映出世道交恶,贤者被弃,佞臣得势,道德友情沦丧,一切均以势利为轴心和转移。李白身受其害,故借赠诗抒感概。第一首诗写完之后,犹未尽意,故又以第二首补足之。两首诗呈现出不同的描写重点,然而又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完整艺术整体。
第一首基本是以七言为主的古体诗,全诗三十二句,可分三个大段落。
第一段共八句,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开端的五言四句为第一个层次,直叙少年不得意,潦倒而无安居生活之业。愿意追随古代任公子之后,投钓东海,钓得能吞进舟船的巨鱼,以饱天下之人,而不作追逐功名利禄之徒。任公子是《芪子》一书中所引用的寓言人物:任公子作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蹉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饱)若鱼者。这四句五字句,一气贯下,借用郦生与任公子的两个典,说明自己志在济世任侠,然而却失意落魄。因而欲步任公子后尘,鄙弃名利,听任自然,相信自己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创主唐代的任氏之风俗。这就使李白少年时的形象与精神,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也暗含着理想与志向同社会现实的矛盾,坚持理想志向,而绝不作势利小人,保持淳美的人性本色。体现着世不容己,己也弃世。他在《古风》(其十三)诗中也表现了与此相似思想:“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暗示出失意落魄的主客观的原因,矛盾的双向性。接着诗人运用七言四句,由前面五言句式的音节短促与凝重,而转为音节舒缓与和平,抒写失意后的生活和行为。经常是饮酒抒忧,追逐徜徉,名山胜水,追求天真的人性美。从此逐渐使壮心与功名相分疏。这正像美好的兰花生在山谷中而不会遭人锄掉一样,保持着它的自然美;又正如围绕高山上端的白云,自由地翻卷与铺张。这四句是写入长安前的生活,暗示出以隐求仕,而不汲汲于功名。追求的是人性自由、适意生活的清真美,从名胜山水风景中吸取美的力量。兰生谷底是反用《三国志·蜀志·周群传》中“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典故,暗示出在朝廷,权贵是容不得贤人君子的。兰花是比况贤人君子的。例如屈原《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描写,比托贤人君子。贤人君子只有在山乡水国才有自己生存的天地,自由的王国。总之这八句诗是李白的自画像,自抒心志,真率自然,发自肺腑。为少年以后与入长安之前的李白作了评介,形神欲出。
全诗的第二段是从“汉家天子驰驷马”至“象床绮席黄金盘”,共十二句,每六句分为一小节,又为一层意思。这段诗的前六句是写李白被征召入京与谒见唐玄宗的隆重盛况。汉家天子是代指唐家天子唐玄宗,派御用的高车四马,像当年汉武帝迎接从蜀地来的司马相如一样,迎接李白。李白进入九重宫门,于金殿上拜谒当今圣君皇帝。皇帝龙颜笑逐颜开,天下人就像沐浴春风一样,受到皇恩的抚育。金殿里左右站班的大臣都高呼万岁,叩拜皇帝、祝贺皇帝征召了一位隐逸失意的贤材。这六句诗是铺陈叙述,但又重点突出,突出皇帝的重视。以赤车驷马相迎,龙颜高兴,群臣高呼万岁等细节,渲染气氛,烘托自己的形象的高贵,超卓拔群,荣耀至极。然而这仅是谒见初的情景。接着诗人又用六句,描绘自己供奉翰林的情景,皇帝垂青,自己大展英才。自己供奉宫内翰林院,执笔草拟皇帝的诏书,受到皇帝的不时注目,焕发出赏识的眼光。宫内藏书的麒麟秘阁威严高峻,自己在这皇帝秘阁中读书,接受皇帝询问,没有谁可以得到这种荣誉,恐怕连看到这高峻的麒麟阁都难。回忆当初承受皇帝恩惠时,进入了右银台门内的翰林院供奉,又独自在金銮殿上草拟皇帝文件。出宫门随侍皇帝,乘有雕饰精美的马蹬与镶白玉的马鞍的御马,在宫中坐的是皇家椅子,用的是皇家御用黄金盘。这六句诗是说明自己志大才高,得到皇帝的信任,满面春风。荣极一时,盛极一时,享受到人臣的极誉。这六句诗采用间接描写,从皇帝眼睛垂顾到环境的烘托,传神地状出自己内心活动和心境昂奋。这与第一段落魄失意的心境构成了鲜明对比,然而这又是不慕名利,以高尚节行与大智大才,自然得到的荣誉。这无疑地是诗意发展、诗情的延伸。
全诗第三段是从“当时笑我微贱者”至“可见羊何共和之”也是十二句,每六句为一小节,为一层意思。前六句是写被逐出长安,饱尝世态炎凉冷暖之苦。诗人说:回想我在朝廷时,原来笑话我出身卑贱而白眼看我的人,现在却一反常态请求我接见,与我交朋友,欢聚在一起。可是当一个早晨我上表章,托病请求还山时,旧日与我交欢相知心的人,没有几个人了。门前送我以礼,随后即关紧门。这些人就是有势就交,无势就改,反复无常。这六句表面上是写自己失势前后的人情关系的变化,透视出势利小人的丑态与趋炎附势的卑鄙灵魂。反映出民族的传统淳朴美德,正被势利小人所践踏,世风浇薄,孕育着社会危机。鄙视、悲愤,感叹之情与探求人生的传统美德等交识在一起,很能感发人意。“当时”,“畴昔”,“今日”相钩连、六句诗意脉一贯,曲折相续,对比鲜明,个性突出。后六句扣题,赞美从弟李之遥始终如一的交情。诗人对他说:对比之下,你的友情如山岳一样始终如一而心不改变,如云雾随着高山一样迷失掉它的所作所为,你不为邪恶云雾所动。云雾是象征着社会炎凉世态,邪恶势力。你与我之间情谊,如当年谢灵运与谢惠连兄弟间关系,才情相用。由此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梦得‘池塘生春草’”这首诗的价值。随着社会阅历之深,而不断地增长它的价值。别后,希望你看到这从遥远地传递去的我的诗篇,也能像谢灵运登临海峤赋诗寄给他的族弟谢惠连一样,和像羊璿之,何长瑜一样的诗友相互唱和。前两句用比喻象征,描绘友情淳真。后四句用典故,谢灵运赏识他从弟惠连之才,相互切磋切琢。当他写《登池上楼》诗时,于梦中见到谢惠连而忽然得到“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羊璿之、何长瑜是谢灵运的诗友,谢灵运又作《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一诗。李白用典比况自己与李之遥兄弟情谊,知音友情。预想李之遥接到此诗,诗友共唱和,又颇感欣慰。第二段所引爆出的悲叹之情迅速转化为平和愉悦,为世上有知音的兄弟而自豪!于此结束全篇,余音绕梁,不绝如缕。
全诗看似平常,无动人的描写,又乏雕饰词句。章法自然,以情运思,构成了失意——得意——失意——自慰的意脉,于平易中数见曲折,自然天成。
全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看似竹筒倒豆,事无巨细,倾泄而出;实则匠心独运,以客观环境与人物描写,兼巧用典故,从今昔对比中,以刻画自己的心象,从两种对立的人格中,歌颂淳朴清真的人格美,以自己与从弟之遥当之。反衬与贬抑势利小人的丑恶人格及其卑鄙的灵魂。进而透视出世风浇薄,贤者被弃的社会悲剧,表现盛唐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这种平易自然,亲切感人,于不见技法中,悟出社会人生的道理,非常深刻。
其二诗则转笔重点写李之遥。宋本《李太白文集》在此诗题自注:“时因饮酒过度贬武陵,后诗故赠。”全诗由此生发,刻画李之遥的性格与形象,及其被贬的原因和诗人评价。在组诗结构上是对前诗作重要的补叙,使李之遥形象光彩照人,与李白正好如一对玉人,相映相衬,天真淳美,然而却都不容于世。
全诗八句,前四句为一个层次,后四句又为一个层次,意脉绵密,严整无痕。
前四句写李之遥思想与性格,作者并不直接述出,而是采用以古托今的笔法,在古今人相映衬中,托出南平太守李之遥如魏晋初的大诗人阮籍,不满意朝臣的倾轧与司马氏诛杀异己,而以酒浇愁,冷眼注视现实,佯狂处世。淳美人性,托之于美酒,而无意于功名利禄,不以专城的郡守职务为重。这与魏晋时的阮籍是十分相似的,故诗人说今古两步兵。阮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听说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这四句以古今对比手法,既刻画李之遥的形象与性格,也暗喻伤酒而被贬。伤酒又如阮籍不满意现实,而又无力挽狂澜,以酒消忧。开端两句平平叙出,但却拓展时空,今古相接,比之单写李之遥却有较丰富的意蕴,赞美之情是今亦是古,今古相重,凝重浓厚。
后四句一转,写李之遥因不顾专城,只爱酒,而被贬武陵。使诗人联想陶潜所写的《桃花记源并诗》,于是就化用这一典故,铸成后四句的美好诗意。诗人说:你去的武陵,就是晋大诗人陶潜所写的桃花源,不知你今后要到这里多少地方寻找桃花源世界。那里的避世乱的秦人,像故旧的相识,出门笑脸相迎你。这四句诗再用陶潜理想与人格托喻李之遥,再次渲染他的人格美,追求理想社会境界。这一用典使李之遥形象增加了光辉。更可贵的是使典故内容与诗意融合无间,塑造一个优美的社会环境。自然美、人情美异于冷峻的现实。注入了诗人的浪漫理想,然而它又植根于现实,并非空中楼阁,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即。
这首诗热情洋溢,气贯全诗,逐层蓄积,赞美,回护,预测,构成感情的流程,心潮逐浪高。古今未来时空相续,关心体贴挚爱之情,无以附加。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不深思就体味不到这种深邃的情思。
这两首诗一长一短,看似不相称,实则各自得体,各尽所职,言近旨远,相得益彰,俱为精品。可参读《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等诗,以对此诗有更深刻的理解。
这是一篇缅怀往事、抒发乱离之感的诗。在诗里杜甫怀念乱前宋中的繁华,伤盛世的消失,讽谕唐玄宗好武功所造成的恶果;忆恋同李白、高适游宋中时的友谊,痛挚友相继死亡,叹自身的衰老飘零。
全诗分四段,开头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宋中地区的繁华;十三句至二十句为第二段写与高适、李白的邀游;二十一句至二十八句为第三段写唐明皇开边之事;最后十四句为第四段,叙写乱离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既有现实经历的生动描述,又有几十年来郁积于心中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此诗纵横古今,雄视万代,畅谈历史,痛砭时弊,总结教训,秀而不冶,艳而不妖。
此诗前十二句,写昔时宋中梁孝王都的风物人情。当时的商丘古城名声仅次于陈留,而与贝州、魏州齐名。这里人口众多,有高楼、大道;水陆交通便利,以至于“舟车半天下”;人们热情好客、行侠仗义。次八句,回顾与高适、李白游览的情景。他们在酒瓮的土台跟前畅饮,“登文台”赋诗,观梁园雁池,望芒砀云烟,追思汉高祖斩蛇起义创业、梁孝王主宾相得作赋。再十句,写唐玄宗当年穷兵黩武、四方征伐,致使生灵涂炭、天下混乱。后十一句,表达对高、李的悲念和哀思。由于岁月流逝、遭逢离乱,朋友已经亡故。李白死于宝应元年(762年),高适也卒于永泰元年(765年),而今自己亦到了衰落之暮年,又“独在天一隅”“系舟卧荆巫”,真是“存殁两呜呼”。诗人以“乘黄”“颜鲍”指高、李,以“凡马”自比,而且常常愿尽“抚孤”的义务,对高、李的尊恭和思念,也表明了三人之间的情深意笃,同时也看出商丘之游对诗人来说是美好,不能忘怀。
前两句一从视觉、一从嗅觉的角度来描写诗人居处的清幽境界。“竹”和“诗”,一为自然之物,一为社会之物,二者本无从比较,但诗人用一个“瘦”字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竹具有清瘦的形象,诗具有清瘦的风格。“瘦”字用得生新,为全诗定下了清瘦的意境氛围。而“入梦香”则将现实与梦境联系起来,梅花夜间在月光的朗照下也喷出清香,已不同凡响,而这香气还伴着诗人进入梦乡,则香气之浓郁、之悠长可以想见。将竹与梅这样的自然物象与诗与梦这样的人为之物炼在一句之中,这就构成了情在景中、景在情中,情景混融莫分的高妙意境。前两句字面上完全没有“月”,但透过竹影和梅香,我们可以感受到“月”自在其中。
在后两句中,诗人便将“月”和盘托出。可怜者,可爱也。当诗人信步庭院时,月光与竹影、梅香是那样的和谐;而回到西厢房时,这月光却不能“下西厢”,这多么地令人遗憾!诗中透露出一股月与人不能互通情愫的遗憾或幽怨的情绪。诗人遗憾或幽怨的是什么?也许是有情人天各一方,不能互通情怀;也许是君臣阻隔,上下无法沟通;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诗人置身此时此景之中的一种朦朦胧胧的感受而已。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