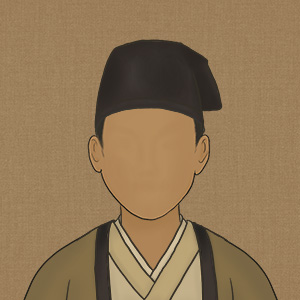这首词上片吊古伤今,抒发词人心中的沧桑凄凉之慨,下片紧承上片的吊古之意,即景感怀,反复咏叹,强烈地抒发了其内心的失意、惆怅之情。全词运用了渲染、烘托等手法,表现了作者贬谪途中去国怀乡的郁闷忧愤之情。
上阙以两个何句作怀古:襄王在何处,宋玉已作古。词以君王与文臣对举,虽是说古事,却不无现实的寓意。首同襄王。“草绿烟深”的氤氲气象代表了政治的清明昌盛,而“何处是”即谓“是何处”,构句已表达了作者的疑问。更何况这“草绿烟深”。当襄王之时,也只是在“梦里”。次间宋玉,将《高唐赋》中神女之句嵌入词中,朝朝暮暮,飞云行雨,又有何人赏识?“几许愁”实形容愁多。在这巫山之地,想那神女之事,发面为两个问句,作者以历史的思考面表达了对于政治清明昌盛、君臣迟契合作的疑惑与犹豫。
下阙承“暮雨朝云”面起,写春天里那漫天飞飞扬扬的花絮。就像人心里弥漫缠绕的愁绪,花絮点点,牵动着愁绪片片,每一点都叫人心痛肠断,而这花絮却不管不问。径自在空中肆意飞舞。城楼下那茫茫的长江水。城对岸那高高的向南山,虽然指示着东去朝中的谒见,南归乡里的团圆,而“胃臣”的心里却充满着悲伤与痛苦。黄庭坚已在遇救出川的路上,不会再有“断肠”之愁。由上片的怀古感慨,引出虽然已经解除了禁个,但是也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的热情。六年的放逐留下了太深的伤痕,他正在考虑退身之事。人在朝廷,并不自由,更有无端的伤害与打击。这是他已经获赦面仍称“羁臣”的缘故。 他在到达江陵之后,坚决上疏向朝廷辞绝京官面请求外任以养家糊口,是缘于这一路上的思考。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由于贺知章这次是以道士的身份告老还乡的,而李白此时也正尊崇道学,因此诗中都围绕着“逸兴多”三字,以送出家人的口气来写的。镜湖是绍兴地方的风景名胜,以湖水清澄而闻名于世。李白想象友人这次回乡,一定会对镜湖发生浓厚的兴趣,在那儿终日泛舟遨游的。为了突出贺知章的性格,诗中不再以宾客或贺监的官衔称呼他,而干脆称他为“狂客”,因贺知章晚年曾自号“四明狂客”。“宾客”到底沾上些官气,与道士的气息不相投合,而“狂客”二字一用,不仅除了官气,表现了友人的性格,而且与全诗的基调非常吻合。
晋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记载的兰亭盛会就发生在贺知章的故乡山阴。而贺知章本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这就使诗人想起了一个故事:据《太平御览》卷二三八记载,王羲之很喜欢白鹅,山阴地方有个道士知道后,就请他书写道教经典之一的《黄庭经》,并愿意以自己所养的一群白鹅来作为报酬。由此诗人说,此次贺知章回乡,恐怕也会有道士上门求书。当年王羲之书写《黄庭经》换白鹅的事情,那又要在山阴发生了。所以,末二句表面上是叙述王羲之的故事,实际上是借此故事来写贺知章,盛赞贺知章书法的高超绝妙。
这首诗基本是李白信手拈来之作,但他一下就抓住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绍兴的镜湖,另一个便是王羲之当年写字换鹅的故事。全诗实际上所写的也就是这两件事。但它们却都恰能表现出友人故乡即山阴的地方特色,同时也都能显示出贺知章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才华所在。李白当时并未去过山阴,因此诗中所谓的“镜湖”、“山阴道士”之类,实际上还都是赠别友人时的一种想象之词。由此可见诗人炉火纯青的诗艺。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