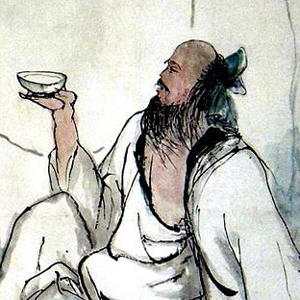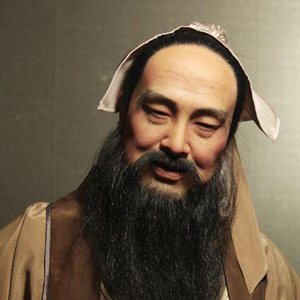此词上片写在游乐之地失去情侣以后,纵然娱乐也悲伤;下片先以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最后以景结情。词中运用反衬、比兴的手法,以乐写哀,用春花怒放之景反衬失却伴侣之悲,用笙歌反衬愁肠欲断之伤,用蝶燕双双反衬孤寂之感,具有民歌格调。全词情景相渗,构思新颖,风流蕴藉,雅淡自然,体现了冯词的特色。
上片写“失却游春侣”、 “独自寻芳”之悲。“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处,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适足添愁,甚而至于举目四顾,一片凄凉,大好春光,亦黯然失色。
“纵有笙亦断肠。”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适足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去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他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因见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蒸儿对对,出入帘幕。
“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彩蝶、燕儿都成双做对,使他怎能再耐得住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青苔半夕阳”一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冯延巳词具有民歌格调者不少,且善于运用比喻、起兴,如《蝶恋花》词:“几日行云何处去?”是以“行云”暗喻浪子,浪子行踪如浮云飘荡,竟然“忘却归来”。由此兴起思妇春怨:“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而这首《采桑子》词,则是以描写蝶燕双飞之乐兴起自身孑然无侣的孤独之感,这种写法在民歌中是经常使用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花前没有了她的陪伴,只能独自在花间徘徊,举目四顾,一片凄凉。纵使笙歌入耳,婉转悠扬,也只能唤起曾经记忆,从而更添感伤惆怅。
满间彩蝶对对,帘间飞燕双双,皆在快乐嘻逐,恩爱相偕。血色残阳笼罩着绿树青苔,怎能再忍受心中悲凉!
注释
纵有:纵使有。
笙歌:笙代指各种乐器;笙歌即指各种乐器演奏声和歌声。
忍:作“怎忍”解。
此词上片写在游乐之地失去情侣以后,纵然娱乐也悲伤;下片先以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最后以景结情。词中运用反衬、比兴的手法,以乐写哀,用春花怒放之景反衬失却伴侣之悲,用笙歌反衬愁肠欲断之伤,用蝶燕双双反衬孤寂之感,具有民歌格调。全词情景相渗,构思新颖,风流蕴藉,雅淡自然,体现了冯词的特色。
上片写“失却游春侣”、 “独自寻芳”之悲。“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处,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适足添愁,甚而至于举目四顾,一片凄凉,大好春光,亦黯然失色。
“纵有笙亦断肠。”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适足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去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他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因见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蒸儿对对,出入帘幕。
“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彩蝶、燕儿都成双做对,使他怎能再耐得住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青苔半夕阳”一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冯延巳词具有民歌格调者不少,且善于运用比喻、起兴,如《蝶恋花》词:“几日行云何处去?”是以“行云”暗喻浪子,浪子行踪如浮云飘荡,竟然“忘却归来”。由此兴起思妇春怨:“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而这首《采桑子》词,则是以描写蝶燕双飞之乐兴起自身孑然无侣的孤独之感,这种写法在民歌中是经常使用的。
这首词的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冯延巳在南唐中主朝出任宰相,其时南唐外有后周侵犯,内部朝政日非。这首词虽然写的是伤春怨别之题材,但有人认为是对当时南唐朝政有所寄慨。
这两首诗与杜牧《赠别》主题相同,即和心爱的姑娘分别时的离别之作,但写法各别。离亭指分别时所在之地,亭即驿站。赋得某某,是古人诗题中的习惯用语,即为某物或某事而作诗之意。诗人在即将分别的驿站之中,写诗来咏叹折柳送别这一由来已久但仍然吸引人的风俗,以表达惜别之情。
第一首起句写双方当时的心绪。彼此相爱,却活生生地拆散了,当然感到无聊,但又势在必别,无可奈何,所以只好暂时凭借杯酒,以驱散离愁别绪。次句写行者对居者的安慰:“既然事已至此,不能挽回,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所希望于你的,就是好好保重身体。你本来已是眉愁腰细的了,哪里还再经得起损伤?”这句先作一反跌,使得情绪放松一下,正是为了下半首把它更紧张起来。第三句是一句惊心动魄的话。除了死亡,没有什么比分别更令人痛苦。这句话是判断,是议论,然而又是沉痛的抒情。第四句紧承第三句,针对第二句。既然如此,即使春风有情,不能因为爱惜长长的柳条,而不让那些满怀着“人世死前惟有别”的痛苦的人们去尽量攀折。这一句的“惜”字,与第二句的“损”字互相呼照。因为愁眉细腰,既是正面形容这位姑娘,又与杨柳双关,以柳叶比美女之眉,柳身比美女之腰,乃是古典诗歌中的传统比喻。莫损也有莫折之意在内。
第二首四句一气直下,又与前首写法不同。前半描写杨柳风姿可爱,无论在烟雾之中,还是在夕阳之下,都是千枝万缕,依依有情。而杨柳既如此多情,它就不会只管送走行人,而不管迎来归客。送行诚可悲,而迎归则可喜。因此,就又回到上一首的“莫损愁眉与细腰”那句双关语。就人来说,去了,还是可能回来的,不必过于伤感以至于损了愁眉与细腰;就柳来说,既然管送人,也就得管迎人,不必将它一齐折掉。折掉一半,送人离去;留下一半,迎人归来,则为更好。
谢灵运的山水诗《入彭蠡湖口》作于作者赴临川(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內史任的途中。彭蠡湖,即江西鄱阳湖。湖口,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据《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心情很不好,这在诗中有所流露。诗中有情、有景,也有议论,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但所写的,有的并不是实写,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如诗中提到的“石镜”、“松门”,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因此可以这样推断: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所感。
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头两句是说,自己乘舟远行,日夜住在船上,既疲倦,又感到厌倦(注意,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
后面两句,是解释为什么“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回:水转的意思。圻岸:曲曲折折的江岸。这两句说,沿途风急潮猛,浪潮遇到洲岛,顿时分流回绕过去,随后又汇流而下;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奔腾向前。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变幻,所以说“难具论”。
接下四句,是追述沿途的景色:“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这两句是写夜景。狖:黑色的长尾猿。浥:湿润。馥:香气。这里用作动词,指闻到香气。芳荪:泛指香草。这两句说,在清朗的月光下,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在湿润的夜露中,饱吸着芳草的馨香。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是说,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颇有新意。时间(春晚)与空间(岩高),远处(绿野)与近处(白云)相对仗,色彩鲜明而谐调,相互映衬,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下两句,是由写景到抒情、议论的过渡,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前、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说,舟行江上,游览沿途景致,思绪万千;从早到晚,浮想联翩。
接下两句,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千念”、“万感”去“照石镜”、“入松门”:“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石镜,《水经注·庐山水》说,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能清晰照见人影,故名。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松门,山名,在江西昌都县附近,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顾野王《舆地志》说:“自入湖(按,即鄱阳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去照一照石镜;我将沿湖而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
以下八句,是作者“千念”、“万感”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三江: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东流入海。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文选·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水别流为派。”理:玄理。古代认为“三”、“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这两句说,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在作者的迷惘中,也掺杂深深的慨叹。
第二层: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金膏:传说中的仙药。水碧:一种玉。这四句是说:江湖中的灵怪神异,因吝惜其珍怪之相,而秘藏其精神魂魄。金膏不再发光,水碧不再变温润。作者以灵物、异人不出,金膏、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
最后一层: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顿。”《千里曲》:曲名,即“千里别鹤”。蔡邕《琴操》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弦绝:曲终。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枉自弹奏了一曲《千里别鹤》,本想借此消忧,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作者的“千念”、“万感”郁积在心,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
这首诗是毛泽东于1955年来杭州疗养时所作。说到杭州,我们马上会联想起“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毛泽东对西湖这一城市名片绝口不提,反将笔墨都花费在杭州周边的群山上,看似有些买椟还珠,但内中却有其原因。其一,毛泽东生性豪爽,与西湖的柔媚绮靡本就扞格,而与雄峙苍莽的山峰甚是合拍,将这种性格融入诗歌之中,便总是倾心于编绘“倒海翻江卷巨澜”、“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壮容。于是我们在他的诗词中总是为“苍山如海”的娄山、“横空出世”的昆仑山、“望断南飞雁”的六盘山和“磅礴”的乌蒙山所打动。当然,他的诗作中也有许多写水的作品,但写水时写的也多是“浪遏飞舟”,如“铁马”、如“雪花”的怒涛,很少描绘平静柔美的水。这与毛主席一生戎马的经历和慷慨豪迈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其二,毛主席时有失眠之苦,在杭休憩期间,医生建议他多进行登山、游泳等活动。游泳时限制较多,相比之下,登山不仅可以放松心情、锻炼身体还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且条件更为便利。杭州的山峰地势平缓,植被繁茂,正是山行放松的好去处,据说毛泽东在杭州疗养时几乎日日携书登山,在山顶阅读休息片刻,再另行觅路下山,那根著名的、胡志明的烟斗都换不来的竹杖便是他在杭州期间为方便登山所制。精神上的契合与休养期间的频繁接触也许正是毛泽东对杭州诸山情有独钟的原因。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描绘了五云山的自然景色和地理位置:五云山上飘飞着五颜六色的云彩,形成一道奇妙的景观,让人大饱眼福;五云山远远地连接着西湖群山,近处轻轻地擦过钱塘江江堤。“五云山”是西湖群山之一。《云栖纪事》云:“山之巅有五色瑞云盘旋其上,因名。”可见,五云山因传说有五色彩云萦绕山顶经时不散而得名。
明人张岱在《西湖寻梦》中对“五云山”有以下描述:“冈阜深秀,林峦蔚起,高千丈,周回十五里……五峰森列,驾轶云霞,俯视南北两峰,宛若双锥朋立。长江带绕,西湖镜开;江上帆樯,小若鸥凫,出没烟波,真奇观也。”说明五云山的自然景色自古有名,历史悠久。“五云山上五云飞”,这是一个让人叫绝的佳句,全句七个字,竟两写“五云”。此处的重复,恰好道出了该山的奇妙传说和动人景色。第一个“五云”言的是山,第二个“五云”说的是云。这种连珠妙语,形象美好,声律动听,在我国古诗中早有垂范。“远接群峰近拂堤”进一步写“云飞”的情况:它“远接”西湖周围的“群峰”,“近拂”钱塘江的大堤,可见“云飞”范围之广。“群峰”,指西湖西面和南面的北高峰、南高峰、美人峰、灵峰山、月桂峰、白鹤峰等诸峰。这里的“堤”,指邻近的钱塘江江堤。“接”为连接,“拂”指轻轻擦过。“接”、“拂”两个动词状写“云飞”的气势,十分传神。“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作者纵行五云山中,观祥云布展,流莺殷勤,忽有所悟,乃在末尾两句中以设问方式叙出。杭州西湖名满天下,赞者在在多有,但赞者越多,游人便越密,喧嚣嘈杂之际,再好的景色,也难免沦为“一无可看”。五云山名气不响,当时离市区又远,罕有人迹,但重峦叠嶂之间,杂花茂树,鸟语莺啼,自有一番清幽之趣。据说毛泽东游五云山的时候,没有通知随行的官员,只带上身边警卫等寥寥数人,轻装简从,从钱江果园沿山径而上,经五云山一直走到上天竺,在四个小时中不与外界联系,处于“失踪”状态,归来之后,兴而有作。毛泽东一生经过大风大浪无数,建国后又日理万机,至杭州本为休养身心。因此,热闹的西湖对他应该已难有什么吸引力;相反,置身山野,享受孤独漫步的心情,恐怕是他此时最需要的。
五云山位于西湖南部群山之中,近与万岭山、琅珰岭、狮峰岭、棋盘山、上天竺联袂,远与南北二高峰对峙,而钱塘江堤则近在山脚下。故次句言“远接群峰近拂堤”。此句将五云山远近水光山色尽揽其中,气势不可谓不宏,境界不可谓不廓;而“接”、“拂”二字,又将“五云山”与毛泽东其他诗中的“怒涛”、“飞浪”等意象区别开来,于刚健之中自饶和婉。
《五云山》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诗人注重描写自身感官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却写得有声有色,让人喜读,令人耐读,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自身感官感受,并且获得了成功。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总离不开人的感觉器官。目视、耳闻、品味……为了形象地描写客观事物,使读者也有切身的感受,作家常常细腻地描写人的感官的种种感受。本诗前两句“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诉诸视觉,后两句“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诉诸听觉,前者为后者作铺垫,重点突出“此中听得野莺啼”。由于作者具体地描写了自身感官的感受,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毛泽东着重描写野莺之啼,意在表现他心中美好闲适的情调。
这是一首思念诗,全诗共八句,写得幽绵悱恻,凄婉感人。
头二句写两人相互愁望,相互思念。“江南江北”,这是两个人的行为,鱼玄机在这头愁望,李亿在那头也愁望。诗人断定李亿也在思念她,即使她的判断有误。她回忆以前的交往,唱或吟诵二人都喜欢的歌或诗句,但这些都没有用,仍然无法缓解思念之渴。 “空”字说明了诗人自己的情态。这两句,诗人将心上人李亿的行为发挥了想像。如果李亿是个扭头便忘的主儿,那么诗人就是可怜的相思。
三四两句写作者看着一对鸳鸯美滋滋地在沙浦享受温情,满眼羡慕。未必真有此景,也许是诗人的浪漫情怀。一对鸂鶒悠闲地飞游于橘林,同样激活了诗人的想像。写了鸳鸯,又写鸂鶒,如此渲染,说明诗人被李亿迷住了,不能自持。
五六两句写诗人等待心上人的情状。“烟”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与下句“月色沉沉”对应,晚上时,江边人家生起炊烟。二、烟波浩淼的意思,傍晚时的一种江色。第二种种解释更靠谱。烟波里传来隐隐的歌声,也许这歌声诗人听辩不清,但她肯定甘愿认为这是一首相思歌,这歌声正合自己的心愿,传到了江的那边,送给李亿。诗人好像入魔了,看到的,听到的,想像的,一切皆变为思念。这一句就是一幅画,想像着诗人坐在江边,托腮沉思,有一种忧愁美。 “渡头”映入了诗人的视线,明知李亿不会来,看着,只是为了圆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一直到晚上,月色沉沉的时候,诗人坐等了一整天。
末二句写虽然两人相隔得不远,但是却无法相见,犹如相隔千万里。“咫尺”,说明在诗人眼里,两人的心是很近的。“千里”,一个江南,一个江北,是地理上的距离。“家家”二字,对诗人是有刺激的,当然她也很想为李亿做棉衣。“远”字与“家家”相连,表现出捣衣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声声都敲打着诗人的心。一个女性的绵情牵系表露无遗。前句中的“歌声隐隐”与这句的“家家远砧”,双双入耳,最后一句写得相当有分量。
这首词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五代手写卷予中无名氏的作品,写的是一个美丽的歌舞伎在暮春哦节的感受。上片写其外表的华美,下片状其内心的悲哀。婀娜的身姿与擦拭不尽的泪珠、掩饰不了的忧愁,相互映衬,达成一种对比中的和谐。
词的上片是写景,作者从动态着笔,既形象地写出了景物的情态,也婉转地表达出了主人公心头的烦闷和怨情,情和景交融在一起。
下片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抒发了主人公心中无限的怨情,一个平常的比喻将主人公的感情推向了高潮。整首词感情质朴而深沉。
这是一首怨词,写恋人远去,给姑娘带来的痛苦。词的上片先从景写起。前两句,勾画了暮春的景色;燕莺啼叫,柳条在春风中袅袅多姿。作者从动态着笔,写得有声有色。尤其是一个“乱”字,既形象地写出了柳条弄春的情态,也显露了主人公烦闷的心情,情和景交融在一起。经过景物的渲染,主人公出场了:“五陵原上有仙娥,携歌扇,香烂漫”。仙女般的姑娘何其美。歇拍告诉人们她这样出场目的,她是要留住那远去之人,可事与愿违,她只是“留住九华云一片”。作者笔锋一顿一折,婉转地表达了主人公心头的怨情。
下片开头一句直写主人公打扮之美,与上片“仙娥”暗映。接着掉转笔锋写道:“负妾一双偷泪眼”,又与上片怨人去暗映。主人公的怨情依然在这一顿一折中代现出来了。作品到此在表现怨情方面,已经非常形象、非常深沉了。可是最后几句作者又展开想象的翅膀,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抒写心中无限的怨和恨:“泪珠若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以真珠比泪珠,可见泪之多;以泪之多烘写伤心之极,从伤心之极正见出怨情之深。一个平常的比喻在这里却把主人公的感情推向了高潮。
这首词揭示了当时中国女性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追求,以及她们这种追求并不为男子所珍视的社会现实。感情直朴而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