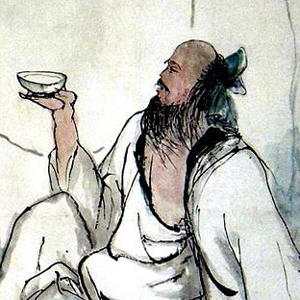诗中诗人将秦军制造的长平之坑与项羽制造的新安之坑这两件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历史事件加以精心的绾合,以涵蓄亭泳、开阖流宕的笔触巧妙地点明秦的暴虐残酷是自取灭亡的根本原因,揭露了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兼并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骇人听闻的深重灾难。全诗构思佳妙、文笔流丽、反思深刻、感叹沉雄。
这首诗的第一部分是前十二句,是回忆长平惨案。诗的头两句如石破天惊,突兀而来。“怪”字,在此是令人惊骇之意。“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日汾流紫”两句,则是用夸张的笔法,极力渲染当时的惨状,因而有惊心动魄之效。“锐头竖子”两句,是诗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价。这两句似乎天外飞来,一反上面惨烈凝重的气氛。诗人似乎从对当时血肉横飞、鬼哭神嚎场面的回想中突然醒悟,以异常轻松的口吻说道:“那白起算得了什么,你们这四十万人为平原君卖命,甘愿找死。”显然是正话反说,孔衍《春秋后语》:“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白起)为人也,小头而锐,敢断行也。”故诗中以“锐头竖子”呼白起。
以下两句又回到惨烈的气氛中。“乌鸦饱宿鬼车哭”一句是写当时深夜,专啄腐肉的乌鸦食饱尸肉,心满意足地缩头栖息枝头;月明星稀,那传说中专收人魂的九头恶鸟(鬼车)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这是何等阴森恐怖的场景。“至今此地多愁云”一句是写现在。那四十万鬼魂不散,使近两千年后的此地,仍时时笼罩在鬼魂组成的阴云之下。此句承上启下,由历史过渡到现实。接下来的四句,又是一组轻松与凝重的对比。当地农夫们并不以为历史上的大悲剧有值得悲痛之处,而相反,以此为谈资。“即令方朔”两句,照应“此地多愁云”。
第二部分是十三、四句,写新安惨案。诗人忽然宕开笔墨,记述了另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公元前206年,楚霸王项羽将秦将章邯部下的降卒二十余万人在新安(属今河南省)城南全部诛杀。诗人显然认为,这是长平惨案的再现。两事相隔仅仅半个世纪。
第三部分是十五、六句,写了赵国与秦国的灭亡的相似。公元前229年,秦国攻伐赵国,秦国私下买通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散布谣言,赵王听信谗言,杀害忠臣,此后仅三个月,秦国大破赵军,赵国灭亡。赵高在秦始皇死后,指鹿为马,专权跋扈,使秦朝迅速灭亡,所以诗人认为,因“赵高出”而使“秦玺”易手。
整首诗运用对比手法揭露了历史事件的惊人相似之处,发人深省。叙事详略得当,详写长平惨案而略写新安惨案,盖二事略类,不必重笔。“郭开卖赵赵高出”句巧妙运用顶针格,写出赵、秦痛史悲恨相续的意味,亦见意匠经营。
此诗与《秦风·无衣》题目及首句皆相同,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完全两样。从字面上看,似觉并无深意,但前人往往曲为之说,《毛诗序》云:“《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云:“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王以武公为晋君,列于诸侯。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釐王果贪其宝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是以诛讨不加,而爵命行焉。”(同上)这一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如程俊英《诗经译注》就认为“恐皆附会”。
从诗意来看,此篇似为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诗人可能是一个民间歌手,他本来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妻子,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温馨。不幸妻子早亡,一日他拿起衣裳欲穿,不禁睹物思人,悲从中来。诗句朴实无华,皆从肺腑中流出:“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七件,可是拣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舒坦,那样美观。”“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六件。可是挑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合身,那样温暖。”语言自然流畅,酷肖人物声口。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凄然伤怀。
对于诗中的句读,旧说两段的起句都作六字句,然今人徐培均认为应标点为:“岂曰无衣?七兮。”前四字为一句,用以自问,后二字为一句,用以自答,诗人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中,抒写了一腔哀思。另外在一些字、词的解释上也颇多歧见。如“七”字、“子”字、“六”字,朱熹《诗集传》以为“侯伯七命,其车旗衣服,皆以七为节。子,天子也”。又云:“天子之卿六命,变‘七’言‘六’者,谦也,不敢以当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朱熹的解释,完全服从于他对于这首诗主题的理解。这首诗既然是述晋武公向周釐王请求封爵之意,那末他就必然把“七”解释为“诸侯七命”,把“六”解释为“天子之卿六命”,而把“子”解释为“天子”。前二者与晋武公的诸侯身份相当,后者则与周釐王的天子地位相称。其说固然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见,然与诗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
从对此诗主题的理解出发,“七”和“六”俱为数词,也可以看作虚数,极言衣裳之多。而“子”则为第二人称的“你”,也即缝制衣裳的妻子。这样的理解,应该是符合诗的本意的。
全诗分为两章,字句大体相同,唯两起变动一个字:“七”易为“六”;两结也变动一字:“吉”易为“燠”。这主要为的是适应押韵的需要。从全篇来说,相同的句式重复一遍,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妙,读者在吟诵中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情韵。
从诗题中不难看出这是一首邀请朋友赴约的诗歌,诗人着力刻画他的书斋的清幽雅致,意在表达对杨补阙的盛情,期待他能如期来访,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对书斋周围景物的准确、细腻的描绘来实现的。
首联中“茅茨”为“茅屋”之意,在这里指的是诗人简朴的书斋。“薜帷”指“薜荔的墙帷”。应理解为墙上长满了薜荔,显示了居所的自然状态。句中用得最妙的是“带”字,应为动词“像带子一样环绕”,与第二句中的“生”相对应,能充分的引发读者的想象:山泉沟壑萦绕着诗人的小屋,浮云彩霞似从小院中升腾而起。此联为全诗的起笔,远观书斋,山环水绕,云蒸霞蔚,如赏人间仙境。
颔联与颈联写书斋周围的景物,“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是此诗是最出彩的句子,二者为倒装句,先突出了竹林山色令人怜爱,而后又以“新雨后”“夕阳时”修饰,指出它们令人怜爱的原因是雨后新绿、夕阳渲染,如此遣词造句,不仅让这些景物融入了人的情感,而且让它们具有了极强的色彩感,使读者很有质感地感受到竹林高山的清秀壮丽。
“闲鹭栖常早,秋花落更迟。”写了这里的鸟与花。白鹭早早的休息,只因一个“闲”字,充分说明了这里的幽静:鸟儿少有人打扰,便可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秋花迟迟不肯落下,只能说明这里的环境适宜它们生长,便可久驻枝头。写鸟、花意在突出书斋环境的清幽雅致、清新宜居。
尾联写诗人早已让家人把那缀满绿萝的小径打扫干净,原因是昨天与杨补阙的约定。一如“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之妙。诗人在上文极力地推崇书斋的环境,意在引出这个约定,希望朋友能如约而至。
此诗用字精准,形式工整,手法独到,写景唯美,表意含蓄,值得后人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