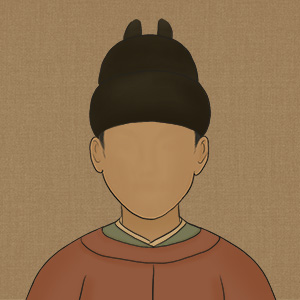“远别秦城万里游”。开头一句,诗人就点出他这次再宿武关非同寻常。秦城,指京都长安。诗人告诉读者,他是从京城来,到万里之外遥远的地方去。这里暗示出他因事罢官流放南方之事。因此这次“远别”意味着和皇城的永别,和仕途的永别:“万里游”也并非去游山玩水,而是被迫飘流到万里之外。诗人这种愁苦心情,在下面的景色描写中透露出来。
“乱山高下出商州”。乱山,指商州附近的商山。商山有“九曲十八绕”之称,奇秀多姿,风景幽胜。“乱山高下”四个字,把商山重峦迭嶂、回环曲折的气势和形貌,逼真地勾勒出来了;一个“出”字,又使静止的山活动起来,使读者仿佛看到绵延迤逦的商山群峰,纷纷涌出商州城。此句是写山,更是写人——写诗人踏着高低曲折的山道走出商州城时的心情。其实,商山似乱非乱,形乱神不乱,它错落有致,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此时此地,诗人已没有闲情细细欣赏,由于他“远别秦城”,心乱如麻,商山在他眼里就成“乱山”了。而满目乱山,又格外烘托出人的心绪烦乱。山与人、景与情交融为一体了。
诗的下两句写夜宿武关的情景。不难想象,诗人此夜投宿武关,想到明晨将出关南去,与“秦城”相隔更加遥远,该是何等愁苦;加以孤馆寒灯,形单影只,非常凄凉。他一定是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然而诗人并没有正面诉说这一切,而是别有巧思,让溪水去替他倾诉:“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古关静夜,溪水潺潺,引起夜不成眠的诗人的遐想:那流过古关的潺潺湲湲的溪水,仿佛是为他的不幸远别而呜咽啜泣;又仿佛是从他的心中流出,载着绵绵无尽的离愁别恨,长流远去。“一夜潺湲送客愁”,溪声、心声迭合成一体了。“关门不锁”四字,尤为神来之笔。雄固的武关之门,能封锁住千军万马,但此时对于淙淙寒溪水送来的愁声,却无能为力,怎么“锁”也锁不住,足见这“愁”的分量之重。一个“锁”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愁”,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来。“一夜潺湲”——整整一夜,诗人不能合眼,这是十分痛苦难熬的。这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地通过对水声的描写,把内心“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恨,曲折细腻地描摹出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量。
这首诗开头两句,写林逋生长的环境。开首即称他们生长在湖山深曲处,山水清澄。后两句讲那里的人物,世外的隐君子是高尚的,就是佣工贩妇也都是冰清玉洁的人。还没有写到林逋,却已经树立了高洁形象。
接下去写林逋高风亮节,源于天性。“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林逋不是与世俗隔绝的人,上文写那个环境里除了“隐君子”外,还有“佣儿贩妇”,正说明他不是与世隔绝的。“神清骨冷”是从《晋书·卫玠传》“叔宝(卫玠字叔宝)神清骨冷”来的。当时所谓骨,指气质品格而言,从神情到品格都清冷。接着,作者写他对林逋的钦仰,这种钦仰在梦中得到反映。他在梦中见到的林逋“瞳子瞭然光可烛”。《孟子·离娄上》:“胸中正,则眸之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瞳仁明亮,说明胸中正,跟神清有关;瞳仁昏暗,说明胸中不正。林逋既是“神清骨冷”,在梦里看到他,那就是“瞳子瞭然”,再夸张一下,便成为“光可烛”,可以照见一切了。这样写,正显示出诗人对林逋的仰慕已经形于梦寐了。这样写,概括了林逋为人的特点。林逋写湖上风光的七言近体诗中,有的反映隐居生活和情思,写得“神清骨冷”。如《湖山小隐》二首之一:“道着权名便绝交,一峰青翠湿蘅芳。”如《湖上晚归》:“卧枕船舷归思清,望中浑恐是蓬瀛。”跟权和名绝交,向往的是仙山,正反映他无意功名。作者赞美林逋,是跟林逋的这五首七言近体诗相结合的。
接下来就谈林逋的诗和书法。“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这里赞美林逋诗善于用字,尤其是咏西湖之作,更为湖上风光传神。“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里用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来比林逋,作者《读孟郊诗》:“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认为孟郊的诗可以跟贾岛(贾岛曾做僧人,名无本)诗比清,不过豪放不及韩愈。作者《祭柳子玉文》称“郊寒岛瘦”,认为贾岛诗的缺点是寒苦。这里指出林逋诗有贾岛之清而无其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句指林逋的书法像李建中,瘦硬有骨力。称赞林逋兼有二人之长而无其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见名家评价)中一方面指出苏轼极为推重林逋的诗和书法,一方面又指出苏轼的评论,像董狐记事的直笔,不作虚美,不推重过分。这样讲是恰当的。
下面再结合他的诗来讲他的高风亮节。“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作者自注:“逋临终诗云:‘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初无封禅书。’”(《宋诗钞初集·和靖诗钞》作:“《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汉武帝的陵园称茂陵。《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相如临死前还在讨好武帝,劝武帝到泰山去封禅,祭天地,告成功。林逋不肯这样做,正显出他的高节。“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白头曲”原为卓文君因其夫司马相如对爱情不忠诚而作,后人多有以此曲为叹老嗟卑、自伤不遇之辞。此处当指后一义。林逋是高士,连《封禅书》也不屑作,更不会悲吟《白头吟》,以自伤不遇。
一结转到杭人对林逋的纪念。“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王世贞称:“始,钱塘人即孤山故庐,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吴人指杭县人,将林逋故居作祠堂,显得低下狭小。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即认为林逋应该和水仙王相配,在水仙王庙里受到祭祀,用一杯寒泉和秋菊来祭。王世贞又称:“因长公诗后有‘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与长公配。”因为水仙王祠早已不存,所以后来改在白香山祠内祭祀林逋,把他跟苏轼相配。
这首诗是赞美林逋,“平生高节”点明主旨在赞他的高风亮节。一开头从湖光到山绿,写环境的美好,从隐君子到佣人贩妇,写人物的“皆冰玉”,这是陪衬。未写到林逋,已光彩照人。结尾变化有力,故称“夭矫”,即另出新意。用“修竹”、“秋菊”来作陪衬,也是取高洁相配。写到林逋本人时,点明“神清骨冷”,显示他的高洁源于天性。又用梦见瞳子瞭然来写他的正直,显出钦仰之情。再评论他的诗和书法。又用司马相如来比,更突出他的高节。这一比又归到他的诗上,回到《书林逋诗后》之题。
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北,《汉书·地理志》新丰县注:“高祖七年置。”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所以新丰这个地名本身便隐含着刘邦之父怀旧的感情。如今诗人与阔别十年之久的友人忽然在新丰市相遇,更易引发起对往日归事的追忆。几杯酒下肚,感情更加激动,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起来。觥筹交错,热泪纵横,其场面是可以想象的。
三、四句忽发议论,“掬诚而出,人人所欲道,恰是人人所不能道。”(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以相逢之喜泪反衬阔别十年之悲泪,又以阔别时间之久长烘托会面时间之短暂,把极其丰富复杂的感情表达得十分充分,使这两句议论成为全诗点睛之笔。此诗艺术上的成功又一次证明,诗歌并不绝对排斥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晬语》)。
《酌》是《大武》五成的歌诗,《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周颂·我将》一篇的鉴赏文字)《大武》五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平定东南叛乱回镐京以后,成王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的史实。当时天下虽然稳定,但仍不能令人放心,所以成王任命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周公负责镇守东南、召公镇守西北,即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楚先祖熊绎此时受封于丹阳(今秭归附近),为子爵,盖亦有协助镇守江南的用意。就《酌》诗的内容而言,前五句是成王歌颂王师的战绩,并对统兵出征的统帅表示感激之情,也就是感激和歌颂周公。后三句是成王任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当然,这时仍是周公摄政,但任命之事则不能不以成王的名义,告庙仪式的主人公也不能不是成王。故该诗的主人公表面上是成王,而实际上还是周公。《酌》向来多被认为是周公的乐舞(如郑笺云:“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也可证实这一点。前人或以为此诗是颂武王伐殷的,但武王并无“周公左召公右”的任命,而且诗中的“晦”也是泛指,不一定特指殷纣王。故不从。诗名为“酌”,《毛序》以为是“斟酌”之意(即“斟酌文武之道”),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恐不妥。“酌”亦可作汋、彴、勺等,就是以勺舀酒灌祭祖先神灵,说明该诗是灌祭祖先时所唱的歌。以歌诗而言则曰《酌》,以乐舞而言则曰《勺》,《仪礼》、《礼记》皆言舞《勺》,《勺》即《酌》。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礼记》)《内则》曰:‘十三舞《勺》。’又:‘成童舞《勺》舞《象》。’……《勺》为武舞,其诗为《酌》之章。按诗歌之节以为舞,列为学校普通教科,故曰成童则舞《勺》舞《象》。”可见《酌》作为乐舞,在当时是与《象》舞一样颇具代表性的。它可以作为《大武》的一成与其他五成合起来表演,就像现代舞剧中的一场,也可以单独表演。具体的舞蹈动作,参见《周颂·我将》一篇对《大武》的全面介绍。
此诗文句古奥,今人读来多不解其妙。若拈出孙鑛“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原为《孙子》中语)的评语以为启发,恐怕读者对其前半部分弦乐柔板般的从容与后半部分铜管乐进行曲般的激昂就会有一定的感悟。欣赏《颂》诗,所当留意之处,就在这如斑驳的古鼎彝纹饰的字句后所涵蕴的文化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