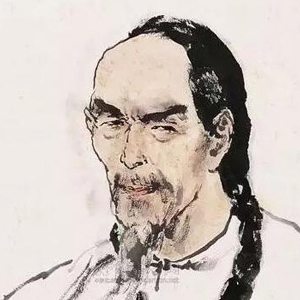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
词的上半阕,作者用了寥寥数笔,就把他从十七岁以来十五年间的坎坷经历粗略地描述了一番。用了两个“纵横”,把自己怀才不遇,箫剑双负的心情形象地表达出来。才“纵横”,是说他的才能大,泪“纵横”,是说他的悲哀多。“箫心”侧重于生活中的各种幽情亲情,“剑名”则主要是大的人生追求和志向抱负,二者“双负”,作者只赢得泪纵横。
词的下半阕,进一步写个人生活之悲:春天来时,连个关心的梦都做不成,不言也人关心自己,反言自己无倾注关心的对象;不说真实的关心,只求做个关心梦,话语中所包含的这些凄怨哀伤,是十分沉痛的。作者又巧妙地用了两个“飘零”,把自己为了功名,南北数次奔波的经历和自我安慰的复杂心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看了词的最后一句话才知道,作者一生漂泊无定,如今虽有些悔怨,但他已不看重这些,因为人生本就是雪泥鸿爪,因为他已信奉了佛教。
据史料记载,龚自珍在道光三年有信佛事。他回乡后在苏州与江沅、贝墉等几个佛门俗家弟子搅到一起,还参加了拜佛诵经。在作者的许多诗歌中,都有他学佛的印记,不少佛经上的语言,被龚自珍写入诗歌中。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学佛来解脱自己考场不得意的失落,这也是当时许多失意文人的通常做法。不过,读了这首词的最末一句,往往有一种苦涩生出,让人同情作者,这正是此词的艺术魅力所在。
金陵(今江苏南京)从三国吴起,先后为六朝国都,是历代诗人咏史的重要题材。司空曙的这首《金陵怀古》,选材典型,用事精工,别具匠心。
前两句写实。作者就眼前所见,选择两件典型的景物加以描绘,着墨不多,而能把古都金陵衰败荒凉的景象,表现得很具体,很鲜明。辇路即皇帝乘车经过的道路。想当年,皇帝出游,旌旗如林,鼓乐喧天,前呼后拥,应是无比威风。此时这景象已不复存在,只有道旁那饱览人世沧桑的江枫,长得又高又大,遮天蔽日,投下浓密的阴影,使荒芜的辇路更显得幽暗阴森。“江枫暗”的“暗”字,既是写实,又透露出此刻作者心情的沉重。沿着这条路走去,就可看到残存的一些六朝宫苑建筑了。“台城六代竞豪华”,昔日的宫庭,珠光宝气,金碧辉煌,一派显赫繁华,更不用说到了飞红点翠、莺歌燕舞的春天。现在这里却一片凄清冷落,只有那野草到处滋生,长得蓬蓬勃勃,好像整个宫庭都成了它们的世界。“野草春”,这“春”字既点时令,又着意表示,点缀春光的唯有这萋萋野草而已。这两句对偶整齐,辇路、宫庭与江枫、野草形成强烈对照,这将它的现状与历史作比较,其盛衰兴亡之感自然寄寓于其中。
接下去,笔锋一转,运实入虚,别出心裁地用典故抒发情怀。典故用得自然、恰当,蕴含丰富,耐人寻味。
先说自然。庾开府即庾信,因曾官开府仪同三司,故称。庾信是梁朝著名诗人,早年在金陵做官,和父亲庾肩吾一起,深受梁武帝赏识,所谓“父子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诗人从辇路、宫庭着笔来怀古,当然很容易联想到庾信,它与作者的眼前情景相接相合,所以是自然的。
再说恰当。庾信出使北朝西魏期间,梁为西魏所亡,遂被强留长安。北周代魏后,他又被迫仕于周,一直留在北朝,最后死于隋文帝开皇元年。他经历了北朝几次政权的交替,又目睹南朝最后两个王朝的覆灭,其身世是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动乱变化的。再说他长期羁旅北地,常常想念故国和家乡,其诗赋多有“乡关之思”,著名的《哀江南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人的身世和庾信有某些相似之处。他经历过“安史之乱”,亲眼看到大唐帝国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安史乱时,他曾远离家乡,避难南方,乱平后一时还未能回到长安,思乡之情甚切。所以,诗人用庾信的典故,既感伤历史上六朝的兴亡变化,又借以寄寓对唐朝衰微的感叹,更包含有他自己的故园之思、身世之感在内,确是贴切工稳,含蕴丰富。“伤心”二字,下得沉重,值得玩味。庾信曾作《伤心赋》一篇,伤子死,悼国亡,哀婉动人,自云:“既伤即事,追悼前亡,惟觉伤心······”以“伤心”冠其名上,自然贴切,而这不仅概括了庾信的生平遭际,也寄托了作者对这位前辈诗人的深厚同情,更是他此时此地悲凉心情的自白。
这首诗寥寥二十字,包蕴丰富,感慨深沉,情与景、古与今、物与我浑然一体,不失为咏史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