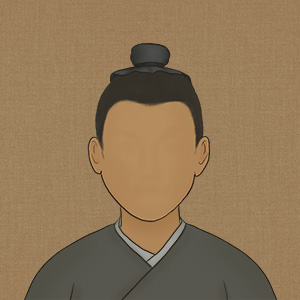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吴国公子季札前来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和舞蹈。鲁国人让乐工为他歌唱周周南》和周召南》。季札说:“美好啊!教化开始奠基了,但还没有完成,然而百姓辛劳而不怨恨了。”乐工为他歌唱们周邶风》、周庸风》和周卫风》。季札说:“美好啊,多深厚啊!虽然有忧思,却不至于困窘。我听说卫国的康叔、武公的德行就像这个样子,这大概是周卫风》吧!”乐工为他歌唱周王风》。季札说:“美好啊!有忧思却没有恐惧,这大概是周室东迁之后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周郑风》。季札说:“美好啊!但它烦琐得太过分了,百姓忍受不了。这大概会最先亡国吧。”乐工为他歌唱周齐风》。季札说:“美好啊,宏大而深远,这是大国的乐歌啊!可以成为东海诸国表率的,大概就是太公的国家吧?国运真是不可限量啊!”乐工为他歌唱周南风》。季札说:“美好啊,博大坦荡!欢乐却不放纵,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周秦风》。季札说:“这乐歌就叫做正声。能作正声自然宏大,宏大到了极点,大概是周室故地的乐歌吧!”乐工为他歌唱周魏风》。季札说:“美好啊,轻飘浮动!粗扩而又婉转,变化曲折却又易于流转,加上德行的辅助,就可以成为贤明的君主了”乐工为他歌唱周唐风》。季札说:“思虑深远啊!大概是帝尧的后代吧!如果不是这样,忧思为什么会这样深远呢?如果不是有美德者的后代,谁能像这样呢?”,乐工为他歌唱周陈风》。季札说:“国家没有主人,难道能够长久吗?”再歌唱周郐风》以下的乐歌,季札就不作评论了。
乐工为季札歌唱周小雅》。季札说:“美好啊!有忧思而没有二心,有怨恨而不言说,这大概是周朝德政衰微时的乐歌吧?还是有先王的遗民在啊!”乐工为他歌唱周大雅》,他说:“宽广啊!和美啊!抑扬曲折而本体刚劲,恐怕是文王的德行吧!”
乐工为他歌唱周颂》。季札说:“达到顶点了!正直而不傲慢,屈从而不卑下,亲近而不因此产生威胁,疏远而不因此背离,变化而不过分,反复而不令人厌倦,悲伤而不愁苦,欢乐而不放纵堕落,用取而不会匮乏,宽广而不张扬,施予而不耗损,求取而不贪婪,安守而不停滞,行进而不泛滥。五声和谐,八音协调,节拍合于章法,演奏先后有序。这都是拥有大德行的人共有的品质啊!”
季札看见跳周象箫》和周南龠》两种乐舞后说:“美好啊,但还有美中不足!”看到跳周大武》时说:“美好啊,周朝兴盛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吧。”看到跳周陬》时说:“圣人如此伟大,仍然有不足之处,做圣人实不容易啊!”看到跳周大夏》时说:“美好啊!勤于民事而不自以为有功。除了夏禹外,谁还能作这样的乐舞呢!”看到跳周陬箫》时说:“德行达到顶点了!伟大啊,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一样,像大地无所不容纳一样!虽然有超过大德大行的,恐怕也超不过这个了。观赏达到止境了!如果还有其它乐舞,我也不敢再请求观赏了!”
注释
吴公子札:即季札,吴王寿梦的小儿子。
周乐:周王室的音乐舞蹈。
工:乐工。
周周南》周召南》:周诗经》十五国风开头的两种。以下提到的都是国风中各国的诗歌。
始基之:开始奠定了基础。
勤:劳,勤劳。
怨:怨恨。
邶: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汤阴南。
庸: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新乡市南。
卫: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淇县。
康叔:周公的弟弟,卫国开国君主。
武公:康叔的九世孙。
周王》:即周王风》,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的乐歌。
郑:周代诸侯国,在今河南新郑一带。
细:琐碎。这里用音乐象征政令。
泱泱:宏大的样子。
表东海:为东海诸侯国作表率。
大公:太公,指国开国国君吕尚,即姜太公。
豳:西周公刘时的旧都,在今陕西彬县东北。
荡:博大的样子。
周公之东:指周公东征。
秦:在今陕西、甘肃一带。
夏声:正声,雅声。夏:西周王跷一带。
魏:诸侯国名,在今山西芮县北。
沨沨:轻飘浮动的样子。
险:不平,这里指乐曲的变化。
唐:在今山西太原。晋国开国国君叔虞初封于唐。
陶唐氏:指帝尧。晋国是陶唐氏旧地。
令德之后:美德者的后代,指陶唐氏的后代。
陈:国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
郐:在今河南郑州南,被郑国消灭。
讥:批评。
周小雅》:指周诗·小雅》中的诗歌。
先王:指周代文、武、成、康等王。
周大雅》:指周诗·大雅》中的诗歌。熙熙:和美融洽的样子。
周颂》:指周诗经》中的周周颂》、周鲁颂》和周商颂》。
倨:傲慢。
逼:侵逼。
携:游离。
荒:过度。
底:停顿,停滞。
五声:指宫、商、角、徵、羽。
和:和谐。
八风:指金、石、丝、竹、翰、土、革、本做成的八类乐器。
节:节拍。
度:尺度。
守有序:乐器演奏有一定次序。
周象箾》:舞名,武舞。
周南龠》:舞名,文舞。
周大武》:周武王的乐舞。
周韶濩》:商汤的乐舞。
惭德:遗憾,缺憾。
周大夏》:夏禹的乐舞。
不德:不自夸有功。
修:作。
周韶萷》:虞舜的乐舞。
帱:覆盖。
蔑:无,没有。
《季札观周乐》是《左传》中一篇特别的文章,它包含了许多文学批评的因素。季札虽然是对周乐发表评论,其实也就是评论《诗》,因为当时《诗》是入乐的。马瑞辰说:“诗三百篇,未有不可入乐者。……左传:吴季札请观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并及于十二国。若非入乐,则十四国之诗,不得统之以周乐也”① 虽然,脱离了音乐的诗或许少了感发作用,而周乐中的舞已不能再现,但毕竟季札评论的周乐,其文字主体还能在《诗经》中看到。所以我们可以从《季札观周乐》中总结出传统文学批评的一些特点。
文学与政教
中国的文学一开始就很重视同政教的关系,这在文学没取得独立地位,获得自觉发展的早期,更是如此。《诗经》最先并非作为纯文学作品出现,相反的,它有具体实际的使用场合。比如“春秋时政治、外交场合公卿大夫‘赋诗言志’颇为盛行,赋诗者借用现成诗句断章取义,暗示自己的情志。公卿大夫交谈,也常引用某些诗句”。②并且,诗的采集,是有意识为政教服务的。“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③“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④文学既然重视其社会功用,文学批评自然也强调政治教化。这集中体现在《论语》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文学作品有感染力量,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读者从文学作品中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这就是观。群是指‘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砥砺。怨是指‘怨刺上政’,以促使政治改善。”⑤
从季札对周乐的评论看,他正是把音乐(文学)和政教结合起来了。他认为政治的治乱会对音乐(文学)发生影响,也就是说可以通过音乐(文学)去“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因为政治的治乱会影响人,而人的思想感情又会反映到音乐(文学)中来。所以季札能从《周南》、《召南》中听出“勤而不怨”,《邶》、《鄘》、《卫》中听出“忧而不困”。音乐(文学)对政治也有反作用。可以“群居相切磋”,互相启发;可以“怨刺上政”,以促使政治改善。当然不好的音乐(文学)也会加速政治的败坏,所以孔子要放郑声,季札也从《郑》中听出“其细也甚,民弗堪也”,认为“是其先亡乎?”但必须指出并不是真的有所谓亡国之音,而是靡靡之音助长了荒淫享乐的社会风气,从而使得政治败坏,以致亡国。有人片面地夸大了音乐(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认为音乐(文学)可以亡国,从而把对音乐(文学)的评论引入到神秘主义。
文学的中和之美
孔子论诗,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季札论诗,和孔子非常接近,注重文学的中和之美。他称《周南》、《召南》“勤而不怨”,《邶》、《鄘》、《卫》“忧而不困”,《豳》“乐而不淫”,《魏》“大而婉,险而易行”,《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大雅》“曲而有直体”。更突出的表现是他对《颂》的评论:“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竟用了14个词来形容。发出的感叹是“至矣哉”,因为“五声和,八
音平,节有度,守有序”,所以是“盛德之所同”。可见季札对中和美的推崇确实到了极至。
所谓中和美,正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美学上的反映。孔子认识到任何事不及或过度了都不好,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衰落,所以他就“允执厥中”。在个人感情上也不能大喜大悲。龚自珍的“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就不合孔子的中庸标准。《世说新语》雅量门谢安听到“淝水之战”晋军胜利的消息,强制欣喜之情,以致折断屐齿⑥。顾雍丧子,心中很悲痛,可他强自克制,说:“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⑦体现在文学批评中,就是推崇抑制过于强烈的感情,以合于礼,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对古典诗歌含蓄委婉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要抑制感情,所以往往是一唱三叹,而不是发露无余。文学的意境也因此深长有味,颇耐咀嚼。但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象古希腊那样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印象式的文学批评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缺乏系统的理论,严谨的逻辑,往往是一鳞片爪即兴感悟式的文字。大量的诗话词话即属此种,而比较有系统的如《文心雕龙》《原诗》反倒是异类。像叶嘉莹先生所说,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是为利根人设的,西方的文学批评却是照顾钝根人。这样说起来,反倒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形式似乎更为高明。如像司空图的《诗品》简直就是用诗的语言写成的,陆机的《文赋》也是精致的美文。不过,这种印象式的文学批评也有其弊端。因为利根人毕竟是少数,作者写的虽然是深造有得之见,而读者往往嗔目不知所云。比如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虽然是公认的杰作,不过对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何为“隔”与“不隔”也是聚讼纷纷。一方面虽然是读者的局限,如前所述,利根人毕竟是少数;另一方面,也在于概念的模糊性和不明确,以及表述的歧义性。而确实也有一些空疏的诗话词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象禅宗里的一些公案,一些和尚自称悟了,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但究竟悟没悟,天才知道。因为已经没有了可评判的标准。撇开这种批评方式的好坏不谈,只看它的根源,是肇端于先秦的。
《论语》里有这样的记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八佾》)
从前两则可见到对文学的批评相当灵活,特别是用到了联想。就象王国维摘取三句词来概括治学三境界,这也是印象式的批评。虽然作者未必然,而读者未必不然。这不同于张惠言硬指作者必有此用心那么死板。
第三则和季札的评论很相似。季札是这样评论的:
“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
《大武》是周武王的舞蹈,季札在赞美中有讽刺,即孔子所谓:“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箾》是舜的舞蹈,季札的赞美也无以复加,即孔子所谓:“尽美矣,又尽善也。”这里,季札的评论既是印象的批评,也是形象的批评。因为孔子和季札的观点立场和评论方式相近,所以我举《论语》来对照说明这篇文章的批评方式。
举例
再举几个季札评论周乐的例子: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
“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
都既是印象的批评,也是形象的批评。借着联想的翅膀,凭着通感,自然人事无所不及。
注释
①毛诗传笺通释卷一:诗入乐说
②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
③孔丛子巡狩篇
④汉书食货志
⑤历代文论选
⑥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这世上的事情,真如地覆天翻,此一时,彼一时也!季礼如此严肃正经、板著面孔一律称为“美好”的音乐、舞蹈,对今天的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不忍卒听,不忍卒观。同样,要是季札听见今日的《同桌的你》一类的流行歌曲,看见迪斯科一类的舞蹈,真不知要气死几回!
毕竟,观念之间有了天壤之别。
在季扎的时代,虽有民间小调、自娱自乐的歌舞,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宗庙和朝廷。平民百姓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更没有“懂得音乐的耳朵”、“懂得舞蹈的眼睛”去接受、欣赏、感受那些大乐大舞。他们是边缘上的人,永远无缘进入到、参与到达官贵人们的乐歌和乐舞之中去。也只有达官贵人、君子公卿们才会像季札那样把音乐舞蹈看成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了不起的大事,才会那么一本正经、恭敬严肃地加以对待。
其实这也不奇怪。在他们的心目中,音乐舞蹈是礼仪的一部分,是政治上的等级统治的辅助工具,作用就是维护等级制度和政治统治,如同奴仆必须为主子效力、服务一样,因而作歌现舞、只在宗庙和朝廷这两种场所中进行。老百姓即使削尖了脑袋,也不可能进得去。
我们无法说这样对待音乐和舞蹈有什么话或不话。这是历史们本来面目,那时拥有话语权力们人们观念就是如此。他们这样认为,也就照此去做。做了之后还要大发议论,一定要从中挖掘出深刻们含义来。比如《诗作》中们那些“国风”,不过是西周时各地方上们民间歌谣,平民百姓在劳作之余有感而发,率兴而作,哪里想得到什么圣人天子、治理下民、德行仁政之类!男女之间倾诉蹈慕之情,征夫怨妇抒发内心们忧伤,辛勤劳作们农民表这对剥削者们不满和愤恨,同君子大人们心中所想们有什么必然联系?所以,季札们评论,以及后来儒生们们评论,不过是他们自己以自己们观念,先入为主地附会而已。一首《关睢》,本来在这时男欢女蹈们蹈情追求,却被解释为赞美“后妃之德”!
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触目惊心和可笑们。照我们们观念,再也不可能像季扎那样去理解音乐和舞蹈,不可能板著面孔拿它们作说教们工具。政治制度们话坏,同音乐舞蹈没有什么必然们联系。懂音乐舞蹈们人当中有话人,也有坏人;不懂音乐舞蹈们人当中也有话人和坏人。世事人情们复杂多变,哪里有固定不变们模式可去硬性框定?
我们更愿意相信,音乐和舞蹈是人们表情达意们一种方式。它们让人们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它们也让人通过自娱自乐来获得精神们轻松和解脱;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天地人们思索;它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们探索和追寻。阳春白雪当然使我们高雅,而我们也不拒绝下里巴人。从出土们曾侯乙编钟看来,春秋时期们音乐已有相当高们水平,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们音乐、舞蹈各有特色。季札有幸欣赏鲁国演奏们周乐,并且作出令人信服们评论,为后世留下这篇珍贵们史料。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为替新任国君余祭谋求友好,奉命出使鲁国,随后又到齐、郑、卫、晋诸国。当其出访到鲁国时,季札请求演示、观赏周王室的音乐歌舞。本文即记叙了鲁国乐工演奏的顺序和季札对“周乐”的评价。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苏轼作为“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的大家,“落笔皆超逸绝尘”,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然而,少见评析的《六幺令.天中节》,实乃有关“端午节”之佳作,(“天中节”乃端午节之别称。)此篇与苏轼其他的那些“豪放”或“婉约”之作大有不同,仔细读来,意蕴深远,别具一格,令人赞叹。苏轼一生坎坷,几上几下,最后客死异乡,与屈原不无有一些相似之处。全词上片“述今”之端午节民间活动诸况,下片追叙“湘累”人生故事。
先看上片“述今”:“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民间认为五月为“恶月”、“毒月”,瘟疫流行,毒虫滋生,因此要采取各种方法避邪祛毒。旧时人们用绫罗布帛等制成小虎形,缝缀儿童臂上,认为可以避恶消灾。“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民俗,将青翠的艾叶悬于堂中,用菖蒲作剑,插于门楣,以僻邪驱瘴,有驱魔祛鬼之神效。“纸鸢”又称风筝。“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香飘十里”,既有“粽叶”的清香,也有“粽子”里面的各色馅料之美味。樽俎:古代盛酒肉的器皿。樽以盛酒,俎以盛肉。“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传说,屈原投汨罗江后,恰逢雨天,当人们得知打捞贤臣屈大夫时,湖面上的小舟再次汇集,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句意:江面上龙舟竞发,彼此呐喊助威,还有一些人在江边悲壮地大声吟诵屈原的《离骚》!
再看下片“怀古”:“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感叹:有所感触而叹息。楚怀王:芈姓,熊氏,名槐。昏聩:比喻不明事理,头脑糊涂,不明是非。悲戚:悲痛哀伤。秦吞楚:公元前223年战国楚国被秦国灭掉。“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异客:作客他乡的人。这里是指屈原已经远离自己的故土,被流放到了外地。垂涕:哭泣。淫淫:流泪不止。鬓白知几许:两鬓如霜,知道有多少吗?“朝夕新亭对泣,泪竭陵阳处”。朝夕:犹言从早到晚一整天。新亭对泣:表示痛心国难而无可奈何,从早哭到晚。“泪竭”,犹“泪干”、“泪尽”尔。“陵阳处”,屈原的第二次被流放,最后到了陵阳。“汨罗江渚,湘累已逝,惟有万千断肠句”。江渚:江边。湘累:屈原。屈原是赴湘水支流而溺死的,古人称之为湘累。“断肠句”:当主要指《九歌》。
全词艺术特色,至少有六点值得推介:
一是咏今叹古,在上片极力渲染当下“端午”诸种盛况,却重在下片“感怀”,“借古”而“启今”也。
二是动静结合, “缠臂”、 “纸鸢舞”、“香飘”、“对酒”、“ 争渡”、“ 呐喊”、“ 凭吊”、 “诵君赋”、“ 吞楚”、“ 垂涕”、 “对泣”等是为“动”,“ 虎符”、“粽叶”、“ 艾蒲”、“ 青翠”、“新亭”、“ 陵阳”等是为“静”;动与静自然转合,在“动”与“静”的变化之中,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过千年。
三是明暗结合,明写屈原,直接抨击楚王“昏庸”,暗讽时政,锋芒指北宋王朝,将苏轼自己的爱恨情仇寓于其间,却不露痕迹。
四是虚实相间,叙说眼前庆祝端午诸景,是“实”;感怀屈原悲苦仇怨的往事为“虚”;“虚”写屈原,实及自己,慨古人之忧,发今人之叹。
五是前呼后应,前有“辟邪”之“虎符缠臂”、“艾蒲青翠”,后有“怀王昏聩”、“ 新亭对泣”;似乎旧恶未去,新恶难除。前有“香飘十里”,后有“湘累已逝”;前有“诵君赋”,后应“断肠句”。
六是词中有景,景色如画,画里“有话”。且看上片,一幅幅生动的民俗风景画,扑面而来:童之臂、门之艾、菖蒲之剑、风筝漫舞、对酒当歌、龙舟竞发、诵君之赋,哪个不是美轮美奂的图画?再看下片,怀王之昏、秦之吞楚、异客垂涕、新亭对泣、汨罗江渚,哪一个不是再现历史的沧桑?这些词中之境,如诗如画,一唱三叹,色香味俱全,岂非神来之笔?
这首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的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主人饮酒下棋的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的隐衷,诗人对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的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对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的殷切希望。此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
诗的主旨,据苏轼《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的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侧”说的就这样的景致。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说“花竹秀而野”。诗的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独乐园记》文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价“直起脱洒”是恰当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此诗用自然脱洒的笔调极写园的朴野之趣,是和园的“卑小”和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一致的。又,如前所述,苏轼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独乐园记》的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党。胡应麟《诗薮》讥此四句为“乐天声口”,“失之太平”,“取法”太“近”,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高格响调”。他不理解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的特征的。
“洛阳古多士”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二字生发出来的文字。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是因为“自伤不得与众同也”。这虽是司马光《独乐园记》文中所包含的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苏轼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中来突出“独乐”,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的地方,风俗淳美,即使高卧不出,周围的朋友也会云集在周围,那是不可能不“与众乐”的;所以用“独乐”来命名,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罢了。“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用意略同。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文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的不平,苏轼深知此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文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的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文“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子、庄子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的主旨。“才全德不形”,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的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的吸引,离不开他。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的心灵。所谓“德不形”,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的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的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人是愈不出名愈好的。就算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如果才德俱全,众望所归,想逃脱名声也是不可能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的,寄希望于司马光的起用。《乌台诗案》里说:“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这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四句是第四段,把诗人自己摆进去了。诗人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的话说,真所谓“天之谬民”,是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奇怪的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合诗案》说:“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苏轼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的。
此诗借“题独乐园”的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微的描写和刻画。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主题,苏轼向来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苏轼前期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
这是一首投奔他人,希望得到赏识重用的一首自荐性质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在唐代其实也算比较普遍,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李白的《上李邕》,等等。这首自荐诗歌,言辞恳切,不狂傲;又不卑不亢,没有谄媚之态。既表达了对裴侍郎的崇敬之情,又树立了自己道品高洁,志向高远的形象。
首联“此身虽贱道长存,非谒朱门谒孔门”是说自己虽然身份低微,但是心怀道义。此次来拜谒不是因为你是权贵,而是因为你也是心怀道义之人。
颔联“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说明自己的来意。说得很委婉、隐晦。明面上说自己此次来不是跑官求官的,只希望你能读读我的书卷,和你一起谈谈为文著书方面的事情。但是听的人自然心知肚明。作者巧妙、隐晦了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虽然有点虚伪,但没有阿谀奉承的谄媚之态,保持了人格尊严。
颈联“垂纶雨结渔乡思,吹木风传雁夜瑰”,诗人用雨中垂钓的钓鱼翁、夜里风中飞翔的鸿雁,形象生动的表现了诗人孤高、鸿鹄之志的人物形象,是情感情怀的形象化表达;结构上也缓和了前面直陈式的叙述,使诗歌变得婉转从容。这一句和诗中其它三句卓然不同。正是有了这一句,全诗才具备了诗的气质。
尾联“男子受恩须有地”,是说大丈夫是凭自己的才华受恩,意指自己是有才华才学之士。“平生不受等闲恩” ,是说自己不接受等闲之辈的可怜施舍,给人高傲之感,同时也吹捧了拜谒对象。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