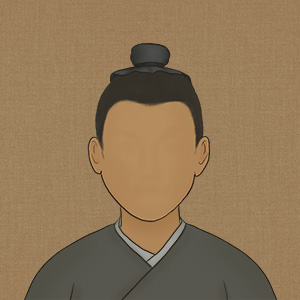文章描述不得志的士子卢生在道士吕翁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美梦,梦中曾一度享尽荣华富贵,飞黄腾达,而梦醒之时连一顿黄粱饭尚未煮熟,揭露了封建官场的凶险和黑暗,讽刺了那些热衷功名、利禄熏心的文士,也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人生如梦的消极出世思想。全文结构谨严,前后以黄粱照应,以黄粱蒸始,以黄粱未熟终,同时穿插一个高人吕翁点拨,一线贯穿,毫无滞碍之感。
故事大意是: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一天,旅途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卢生自叹贫困,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枕上。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五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八十岁时,生病久治不愈,终于死亡。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此即“黄粱一梦”的由来。
《枕中记》讽刺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社会官场。贫寒之士卢生慨叹自己生世不谐,不能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吕翁使他入梦,在梦中这一切向往皆得以实现:与高门大族联姻,进士及第,青云直上,出将入相,受封国公,子孙满堂,年逾八旬,寿终正寝。然而作者并未让他的仕途一帆风顺,正当卢生双功齐建,功成名就之时,“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当他任中书门下章事十余年,号为贤相时,“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经过两次打击,甚至下狱几死的卢生,被减死罪,重封燕国公后,“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如此不似当初建功立业,却耽于声乐。这是作者以自身的经历感受到整个世风如此,因为居官不到两载即因党争株连而遭贬的沈既济,对官场斗争是深有感触的。“晏与炎,相继覆败,其必出于党争倾陷可知,亦何至皆入死罪?……德宗之猜忍,则于此可见矣,贞元后之失败,非无故也。“唐中期朝廷内部斗争,昏君奸相与忠臣良将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的。《唐纪·玄宗天宝十载》描述昏君奸相造成的腐败局面:“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为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塞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玄宗以后,肃宗代宗德宗无不昏庸猜忌,任用奸臣佞相,把持朝政,忠良被贬被杀,因此,作者写卢生终于醒悟:世人共浊己独清时,便会被贬被杀,而与世同浊,便会荣华富贵,福禄寿禧可见,卢生由执于功业而到耽于荒乐,非本性如此,黑暗之官场使然,作者这里是将讽刺的矛头指向社会,指向官场。
主人公因对现实不满而本人亲自入梦,感受梦中和现实的差别。梦前的卢生“短褐,乘青驹“,一副贫寒书生的样子,梦中的他曾拥有功名富贵,但有“下制狱“的危险,为此梦中的他甚至后悔“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梦中和现实即形成对比。另外,卢生入梦之前,主人方在蒸黍,梦中经历一生荣辱成败,醒后主人蒸黍未熟,突出辉煌的一切,不过是短暂的一梦。通过这种对比,强调了人生如梦,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莫不如此而已的结论。
作品构思新颖,对比鲜明,感染力很强。作品极力渲染卢生娶妻,“女容甚丽”,屡建奇功,“立碑颂德”,富贵之极,显赫之至。然后,笔峰陡转,点破这一切原来都是白日梦。梦中卢生何其富贵、显赫,而现实中卢生则极其困顿、贫寒,形成天壤之别的巨大反差。虽透露出人生似梦、富贵无常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却也给予追名逐利之徒以委婉嘲讽,发人深思。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大鹏是李白诗赋中常常借以自况的意象,它既是自由的象征,又是惊世骇俗的理想和志趣的象征。开元十三年(725年),青年李白出蜀漫游,在江陵遇见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称李白“有仙风道骨焉,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后改为《大鹏赋》),自比为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李白诗中还有一首《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据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序》云,李白“赋《临终歌》而卒”。后人认为可能就是这首《临路歌》,“路”或为“终”之误写。可见李白终生引大鹏自喻之意。按此诗语气直率不谦,故前人有疑非李白之作者,亦有信为李白之作而辨之者。参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此诗题解。
全诗开篇激昂高调,前四句均以“大鹏”自比。“大鹏”这一意象经常在李白的作品中出现。大鹏是《庄子·逍遥游》中的神鸟,传说这只神鸟其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其翼若垂天之云”,翅膀拍下水就是三千里,扶摇直上,可高达九万里。大鹏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是自由的象征,李白深受其影响,故而李白的作品中永远有最浪漫的幻想,永远充满对权贵的傲视和对自由的追求。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以大鹏自比,描写了传说中的神鸟大鹏起飞、下落时浩荡之景象,更是表现出了诗人李白此时豪情满怀、直冲青云之志向。李白在诗中第三、四句写到:“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即使大风停下来,大鹏落了下来,也会在江湖激起波澜。如果李白自比大鹏,那么李邕自然就是大鹏乘借的大风,李白在这里言明即使将来没有了李邕的相助,他也能在政坛造成非凡的影响。这种非凡的胆气不得不用一个“狂”字来总结。
诗的后四句,是对李邕怠慢态度的回答:“世人”指当时的凡夫俗子,显然也包括李邕在内,因为此诗是直接给李邕的,所以措词较为婉转,表面上只是指斥“世人”。“殊调”指不同凡响的言论。李白的宏大抱负,常常不被世人所理解,被当做“大言”来耻笑。李白显然没有料到,李邕这样的名人竟与凡夫俗子一般见识,于是,就抬出圣人识拔后生的故事反唇相讥。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两句意为孔老夫子尚且觉得后生可畏,你李邕难道比圣人还要高明?男子汉大丈夫千万不可轻视年轻人呀!后两句对李邕既是揄揶,又是讽刺,也是对李邕轻慢态度的回敬,态度相当桀骜,显示出少年锐气。
其实历史上李邕本人亦是一个侠义豪迈、天纵英才的人物,而且对后辈多为照顾。对于这样一位名士,李白竟敢指名直斥与之抗礼,足见青年李白的气识和胆量。“不屈己、不干人”笑傲权贵,平交王侯,正是李太白的真正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