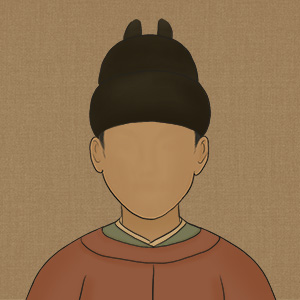此词的作者生活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之际,他曾做过后蜀的永泰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可说是位极人臣。然而蜀主孟昶究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后蜀终为赵宋所灭。鹿虔扆品性高洁,不仕新朝,得到了自由之身。然面,当他重游故地,看到当年的雕梁画栋变成了而今的残垣断壁时,不觉“中心摇摇”,一种强烈的黍离之悲油然升起在心头。
笔下全是景,景中全是情,是这首词的最大特点。在词人的笔下,完全是一片荒凉而凄清的景象。词人虽也写“金锁”、“重门”、“绮窗”、“翠华”、“玉楼”,但这些不过是以当年曾经的繁华富丽来反衬此时的悄寂荒颓。揭示出正是这国破家亡的惨史才使得昔日的繁华如被雨打风吹去。在词中,词人不用一句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而是笔下全是景,几乎将其目之所及、身之所感的景物写尽了,但“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诚然,没有单纯的写景,写景的目的总是为了抒发一种情怀,在这首词中,词人抒写的是他的亡国之隐痛,因而景中蕴含着的又全是一片哀情。
王国维说:“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在此词中,词人没有让自己露面,然而在词的字里行间却隐现着他“行迈靡靡”的身影,喟叹着他“悠悠苍天,彼何人哉”的心声。“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本是自然的场景,此刻却染上了词人的心绪,于是,又升发出一种物是而人非之感。就这样,“绮窗”带上了词人的愁而对秋空,“藕花”含蕴了词人的哀而泣香红,暗伤亡国,一缕幽恨,都赋予秋空、野塘。将无知亦无情的景物写得如此富于情致,正是词人内心无限悲怆使然。“神于诗者,(善将情、景)妙合无垠”,作者以无一字写情,而笔笔关情的高超技巧将内心的黍离之悲抒写得如此有致,使人们仿佛可以从他笔下的景物中看到他忧患的面影,听到他悠长的叹息声
这是一阕文人写的最早的爱国词。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引倪元镇《云林》称此词“而曲折尽变,有无限感慨淋漓处”。谭献《镡评〈词辨〉》卷二:“哀悼感愤。”所谓“曲折尽变”,是因为它表示“感慨”、“感愤”,并非秉笔直书,而是通过“抚今追昔”移情于景,借景抒情,并以“烟月”、“藕花”无知之物,反衬人之悲伤,烘托、渲染,而愈觉其悲。
雪窦,即雪窦山,在今浙江省奉化县西60里,海拔800米,为四明山的分支。唐代曾在此建寺,原为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今虽废,但乃有不少景点。
邓牧于癸巳(1293)春暮二十四日游雪窦山。这篇游记留下了他的踪迹,也使我们今天能一睹七百年前的雪窦山的风光。
游记的第一部分,作者用四段文字,记叙由石湖(今江苏省吴县盘门西南十里)至雪窦山的行程,约占全文的五分之二。记叙游程,交待行止,使景点所处及周围环境了然于纸,也为后来的探奇访胜者导游,这种笔法已经形成我国游记散文的共同特点。但是象本文,开篇在交待行程上就如此泼墨,还是不多见的。
但细细读来并不乏味。沿途几百里,水陆兼程,由石湖起程,舟行二十五里达江,“江行九折达江口”,入溪水又行“九折达泉口”,水浅处,“曳舟不得进”,则“陆行六七里”,经两天两夜后,又涉小溪大溪,抵达溪口才转入山路。这段朴实的文字,不仅写出了路途遥远曲折,而且在长途跋涉中,使人看出作者“闻雪窦游胜最诸山”后,就不殚旅途险阻,而“一意孤行”的勃勃兴致。
江浙一带,素以风景优美着称,沿途几百里,自多奇山异水,一路揽胜,倒也不觉乏累。作者用悠闲的笔调写道:“视潮上下,顷刻数十里”,轻舟飞驰的畅快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一会儿舟行大溪上,深沟险壑,森然可怖。一会儿巨石临水,“若坐垂踵者”,多么悠闲自在。一会儿溪水环山,自高处坠入山涧,远远望去,犹如自蛇奔赴大壑,气象万千。更有“桑畦麦陇,高下联络”,田家村舍,“隐翳竹树”,樵夫牧童,追逐嬉戏,颇有些桃花源的味道。作者很想知道这地方的名称和历史,无奈村民不谙吴语,无从得知;遗憾的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此看来,作者对这一段行程不惜笔墨,是有所记而记的,并非闲笔。
从第五段起转入山路,开始登临雪窦山。作者着重记叙了雪窦山观亭,千丈岩观瀑和妙高台观石。
雪窦山观亭。作者移步换景。上到第二座山峰,这里景亭棋布,各揽一胜。因此作者没有把“亭”作为描写对象,而把镜头转向了它们周围的景物。隐秀亭处是万杉藏秀;漱玉亭下是甘甜清泉;锦镜边海棠围池,花影映水,灿烂如锦秀;寒华亭内题留荟萃,文采精华;大亭上有宋理宗的“应梦名山”御笔……一路观光,美不胜收。
千丈岩观瀑。千丈岩,顾名思义,这里崇岩壁立,谷深千丈,是个险峻之地。作者登临“崖端”,攀树“下视”,以至“目眩心悸”,历险逐胜之情跃然纸上。飞雪亭观瀑,是千丈岩的着名景观。“初若大练,触岩石,喷薄如急雪飞下。”寥寥十余字,写出了瀑布自崖顶飞泻潭下的壮观景象:它自锦镜直径十余丈的大园池喷薄而下,始则宽如大练,继而与岩石相激,珠玑四溅,细若飞雪,纷纷急下。沾湿衣襟,着实让人心醉。“情以物生”(刘勰《文心雕龙·铨赋》),“辞以情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这一惊一喜引发了作者的感慨。他唇吻翕动,刚要启口,环顾四周,竟没有一个知音,不禁“怅然久之”。他想说什么呢?”此时此刻作者决非是要赞山吟水,他要“清谈玄辩”(多指玄妙的哲理)。作者32岁时南宋灭亡,怀着悲愤的心情,拒不出仕;放浪山水以后,逢寓止则“杜门危坐,昼夜为一食”(《洞霄图志》),以后隐居洞霄宫,也过着“身不衣帛,楮御寒暑”(《伯牙琴》)的清苦生活,直到在超然馆无疾坐化,终不改志,走的是一条多么艰险的人生之路啊!虽有谢翱、周密(也是抗节隐逸之士)二位好友,但都未曾同游,且境况相似……在伤时感遇的慨叹中,流露出了作者的幽愤与渴望。
妙高台观石。这里山石岩岩,奇形怪状,作者就极力描摹它们的形象,盛赞它们“自然动人”,远远胜过“观花”。刚才的“怅然”云散了。其实,这种伤时感遇之痛是切肤入髓的,稍有引发,就由衷而出。上文有三处写到琅琅书声:一处是药师寺的寺僧读书声,一处是溪口大废宅中传出“诵声”,一处是雪窦寺的主僧少野读诗声。听到这些亲切的读书声,作者不仅驻足谛听,还要辩析一番,评论一番。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之道是修身积学,齐家治国。作者在《逆旅壁记》中说:“余家世相传,不过书一束。”这位书香了弟对读书声倍感亲切与惊喜,正反映了他虽身在山水,但终难忘情于世事人道。可见,寄身荒野乃是出于无奈。作者惟恐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曲,特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伯牙琴》,大概就是耿耿于此吧。
邓牧在自叙传中说:“以文字请,每一篇出争传颂之,非其人求之厚馈弗为。”我们不必对他索取厚馈加以厚非,且看他对自己的文字是何等的自重。总观全文,作者很善于把握景物的特点:雪窦山的亭,千丈岩的瀑,妙高台的石,各具特色。闽浙一带,三江九溪,苍山与碧水,总是相依相伴,雪窦山更是如此。但作者写水,各择其妙:或写形,如“白蛇蜿蜒”;或写声,“溪声绕亭”;或写味,“饮之甘”;或写动,“大溪薄山转”;或写静,“花时影注水中”;总之,使人领略到每一景物的独胜之处。
作者描摹景物的形态,不拘一格。妙高台的山石:色,“或绀(gān微带红的黑色)或苍”。形,有的象扣着的盂;有的象丢弃的帽子,委屈地躺在地上;有的象蛟跳跃;有的象兽蹲踞。远处的山峰,“青岚上浮,若处子光艳溢出眉宇”--青霭缭绕,阳光穿射,色彩缤纷,简直象个蛾眉秀目,脉脉含情的少女,再美的花也比不上。这段不足百字的景物描写,竟川了动情结合,比喻拟人,远眺近观,对比衬托……直到穷形尽相方才收笔,如此的精细酣畅。
寄情于景,寓志于物,是我国游记散文的传统,到唐宋时期,已经达到“物我双会”的境界。本文作者把自己的伤时感怀都融注在景物之中,自然而亲切,令人心领神会。
诗中用虎门形势的雄壮险要和遗垒的残破颓败,当年抗击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和眼前侵略者的嚣张狂暴作对照,抒发出忧时伤世的愤慨心情。全诗文辞瑰丽,风格雄浑。
“粤海重关二虎尊”写景,由远及近,由海及山,勾勒出虎门的地理形势。一个“重”字写出了侵略者难以突破的层层险峻防御关口,而一个“尊”字又写出了“二虎”不可侵犯的雄伟气势。在如此形势的战略要地作战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定能大获全胜。从字面看是写景,但在写出这样的景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诗人为什么这样写的主观情绪,“重关”与“二虎”的客观形势与勇猛必胜的主观信念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万龙轰斗辜何存”,不仅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士抵抗英军侵略的英勇战斗最终未能抵御敌人的入侵,而且在此抵抗敌人的战斗业绩也永远成为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致使虎门炮台被英国侵略者轰坏并拆毁防御工事。
诗人用“万龙轰斗”四字追叙当年的英勇行为,表现了诗人对爱国将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战的赞颂和缅怀,而“事何存”的反问强烈地谴责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纵使有英勇不屈的将土有虎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雄关,然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使侵略者倍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使中国的危机不断加深,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至今遗留下来的唯有残石断垣余垒,破败不堪,一派凄怆苍凉,只见白浪滔滔、汹涌而过,虎门似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雄风伟力,虎山完全被“白浪如山”的气势所吞没。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但诗人并没有直言抒发,而是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嫉愤、对当年辉煌抗战业绩高然无存的哀惋、对民族危亡深切忧患等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最后这两句眼前凋零残败景象的描述之中。
全诗四句,只有一句言事,其余三句均写景。同是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但战前的景象与战后的景象截然不同,形成虎虎生气与残败不堪的强烈对比,这就在于诗人移情于景所致。诗人对战与降的态度不同,对战前和战后历史的心情不同,就在不同的景象描写中即对景象的不同描写中蕴含着诗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评价。虽然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发感情,但思想感情却表达得淋滴尽致,尽在景象描述之中,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