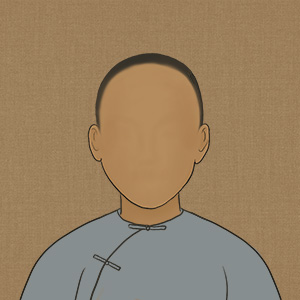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言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
此词上下阕都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写得明白如话而又清新幽默。上阕写博山道中的外景。南临溪流远望如庐山之香炉峰,足风其景秀美。上阕头三句,写得颇有季节特点,特别是“骤雨一霎儿价”,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夏日阵雨的特点。阵雨过后,斜阳复出,山水林木经过了一番滋润,愈加显得清新秀美。“风景怎生图画”一句,以虚代实,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同时又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青旗”二句,点出了酒店,交代了作者的去处,既与下阕“午醉醒时”相呼应,同时又点出作者闲居生活感到百无聊赖。从词的意境上说,这二句把画面推向了更深一层,别有一番风致。七、八二句是抒情,说只想在山色水光中度过这个清闲的夏天。句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
下阕开头,写酒家周围的环境。“午醉”一句,同上阕“青旗”相呼应,“松窗竹户”当为酒家的景致。作者酒醉之后,在这里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只见窗外松竹环绕,气度萧洒脱俗,十分幽雅。这首词的上下阕在时间上有个跳跃,由“午醉”加以过渡,从而增强了上下两阕的紧密联系。“野鸟”二句,运用传统的动中取静的写法。唯其动而愈见静。辛弃疾正是运用了这种手法,把酒家的环境写得十分幽静,但正是通过这“静”来反衬出他心中的不平静。紧接着由“野鸟”带出白鸥,由景入情,写得十分自然。作者用了“鸥盟”的典故。鸥盟即是隐居者与鸥为伴侣。意在表明自己决心归隐,永与鸥鹭为伴。“却怪”二句极显诙谐,旧友白鸥怎么啦?觑着词人欲下不下,若即若离。因而最后三句接着问,莫非是新来变了旧约?这三句向白鸥提问,显得十分幽默,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襟怀,流露出他孤独寂寞的况味。此外,这三句笔势奇矫,语极新异,令人玩味不已。
作者隐居带湖,主要是由于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多少带有一点无可奈何。这种浪迹江湖的生活,并非是他所追求的。因此,他在表现一种超脱的闲适之情时,仍然不时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不平静来。从整首词来看,有些句子显得悠闲自得,实质上是作者深感百无聊赖而自作宽解罢了。一种希冀用世的心绪,还是时隐时现的表露出来。
在这首词的小序中,作者标明“效李易安体”,而李易安即李清照,是宋代婉约词的大宗,这说明,作者虽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在“龙腾虎掷”之外,又不乏有深婉悱恻的情调。他的这首“效李易安体”之作,着重是学易安“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金粟词话》)的特色。其中诙谐幽默的成份,则纯属自己的个性。这正为读者提供了一位伟大作家“博取”的例证。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