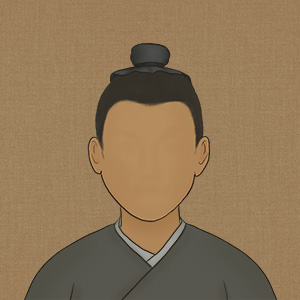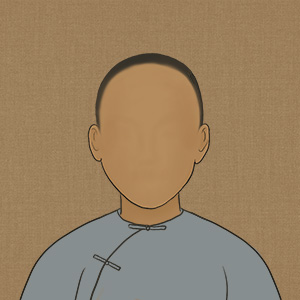此诗写观看祈雨的感慨。通过大旱之日两种不同生活场面、不同思想感情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水浒传》中“赤日炎炎似火烧”那首著名的民歌与此诗在主题、手法上都十分接近,但二者也有所不同。民歌的语言明快泼辣,对比的方式较为直截了当;而此诗语言含蓄曲折,对比的手法比较委婉。
首句先写旱情,这是祈雨的原因。《水浒》民歌写的是夏旱,所以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此诗则紧紧抓住春旱特点。“桑条无叶”是写春旱毁了养蚕业,“土生烟”则写出春旱对农业的严重影响。因为庄稼枯死,便只能见“土”;树上无叶,只能见“条”。所以,这描写旱象的首句可谓形象、真切。“水庙”即龙王庙,是古时祈雨的场所。白居易就曾描写过求龙神降福的场面:“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家家养豚漉清酒,朝祈暮赛依巫口。”(《黑潭龙》)所谓“赛”,即迎龙娱神的仪式,此诗第二句所写“箫管迎龙”正是这种赛神场面。在箫管鸣奏声中,人们表演各种娱神的节目,看去煞是热闹。但是,祈雨群众只是强颜欢笑,内心是焦急的。这里虽不明说“农夫心内如汤煮”,而意思已全有了。相对于民歌的明快,此诗表现出含蓄的特色。
诗的后两句忽然撇开,写另一种场面,似乎离题,然而与题目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说前两句是正写“观祈雨”的题面,则后两句可以说是观祈雨的感想。前后两种场面,形成一组对照。水庙前是无数小百姓,箫管追随,恭迎龙神;而少数“几处”豪家,同时也在品味管弦,欣赏歌舞。一方是惟恐不雨;一方却“犹恐春阴”。惟恐不雨者,是因生死攸关的生计问题;“犹恐春阴”者,则仅仅是怕丝竹受潮,声音哑咽而已。这样,一方是深重的殷忧与不幸,另一方却是荒嬉与闲愁。这样的对比,潜台词可以说是:世道竟然如此不平啊。这一点作者虽已说明却未说尽,仍给读者以广阔联想的空间。此诗对比手法不像“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那样一目了然。因而它的讽刺更为曲折委婉,也更耐人寻味。
开篇二句“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点明从军远征的目的。作者是个胸怀大志的人,这次出征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因此,他对这次从军出征抱有很大的希望。一个“遐”字、一个“讨”字,写出了这次出征的浩浩荡荡、堂堂正正,显现了诗人内心的艰巨感和自豪感,从而为作品奠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基调,并成为全诗的主旋律。
然而诗人并没有立即从正面抒写自己的豪情壮志及令人神往的战斗生活,而是笔锋一转,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沿途的景物。“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坻。”这二句既写出了从军生活的紧张气氛,又写出了因离家愈来愈远而产生的一种惆怅感。“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既是眼前的实景,又是诗人思乡之情的自然流露。不仅如此,秋风中蟋蟀的哀鸣,暮霭下孤鸟的乱窜,更增加了内心的凄凉与悲伤。诗人把暮色中的行军、夕阳下的桑梓及蟋蟀、孤鸟等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典型的“悲秋图”。这样的景物描写,融情于景,以景写情,情与景妙合无间,浑融一体,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面对如此凄凉景象,诗人的感受是:“征夫心多怀,恻怆令吾悲。”离情别绪,人皆有之,而出征的将士则尤为强烈。这是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横尸疆场,即便能侥幸生还,也很难保证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因此生离死别的痛苦不能不咬噬他的心灵。为了排遣悲伤的情绪,诗人“下船登高防”,登上高高的河堤,久久地凝望着远方的故乡,以至被秋露打湿了衣裳。登高不仅没能销忧,反而感到一股寒意阵阵袭来,感情的浪涛不停地在胸中翻腾,无法遏制。“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柔肠寸断,难以成眠,甚至连个说心里话的人也没有。诗人好像被孤独、寂寞的气氛所包围,跌进了痛苦的深渊。这可以说是思妇游子的一种共同的心境。作品以简洁、朴实的语言,形象地勾画出抒情主人公悲怆难抑的情态。
但是作者毕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志士,决不会长久地沉溺在儿女之悲中。因此,诗人笔锋又转,唱出了时代的音响:“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这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将作者从沉溺中惊醒,也如狂飙突起,喷泻出慷慨激昂的情怀,悲伤、低沉的情绪荡然无存。在国事与家事,事业与私情的天平上,作者作了理智的抉择。
慷慨悲凉,是建安诗人的共同特色,该诗就体现了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很善于运用感情起伏的反差,来突出内心的激情,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作品先通过景物描写,创造出一个典型的艺术氛围,有力地烘托了诗人孤寂、凄凉、悲愁的心境,使诗歌的情绪跌入低谷。接着急转直上,又把情绪推向高潮: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可以说,这种落差越大,就越能突出诗人慷慨豪迈的情怀,也就越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该篇采用叙事的手法,正所谓“词宜抒情,或直发胸臆,或假以兴象,而叙事者少见”。所以显得更为奇妙。
上片情语出之于景语,写女子意兴阑珊之貌。首句点明时间是黄昏,正是夕阳西下时分,朱帘斜斜地垂挂在软软的金钩上,一副颇无心情的懒散样子。“倚阑无绪不能愁”是说这位女子倚靠着阑杆,心绪无聊,而又不能控制心中的忧愁。此三句以简洁省净之笔墨描摹了一幅傍晚时分深闺女子倚栏怀远图,为下阕骑马出游做好铺垫。
下片亦刻画了一个小的场景,但同时描绘了一个细节,活灵活现地勾画出这位闺中女子怀春又羞怯的形象。“有个盈盈骑马过”一句,清新可喜,与李清照“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有异曲同工之妙。特别是“盈盈”一词,形容女子,有说不出的熨帖生动。“薄妆浅黛亦风流”一句则凸现了她的风情万种,“薄”、“浅”形容她的容貌,“亦”字说她稍加打扮就很漂亮。末句言,“见人羞涩却回头”。这只是少女一个极细微的,几乎叫人难以察觉的动作,词人却捕捉到了,轻轻一笔,就活灵活现地勾画出闺中女子怀春又娇羞的复杂心情。可以说骑马少女薄妆浅黛羞涩回头的神态,把原本显得低沉的夕阳、小楼、斜挂的朱帘、软垂的金钩及无聊的心绪衬托为一幅情景交融、极具美感的画卷,读来口角生香,有意犹未尽之感。
这是一首咏燕之作。燕子作为春天的信使,美丽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赏爱,所以咏燕之作代不乏人,《诗.邶风.燕燕》,南宋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词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特别清拨之作。张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显然汲取了我国古代咏燕诗词的文化底蕴,尤其可以看出他对史达祖《双双燕》词在艺术构思上的某些传承。不过,作为清代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流文学宗师,张惠言始终不屑于拾前人牙慧,始终欲有创立和开辟,他的朋友鲍桂星就说他:“独念君生晚近时,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受经堂汇稿序》)。所以,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虽有汲取,但多新变,展示更多的是他独立不偶的心性以及别出心裁的艺术追思,且又传达出他游踪漂泊而又寂寞孤苦的人生遭际。
农历一月底二月初的“春社”时节,“满城”均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那沥沥雨丝与潇潇雨声唤起一双燕子无家可归的“新恨”,因为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年年迁移的侯鸟燕子,又要开始新的漂泊。然而,此时此刻,燕子还不知道家在何方。春天的花朵还是那样灿烂,春天的杨柳还是那么葱翠,它们重重叠叠隔断了通向闺中思妇居住的“红楼”小径。燕子隐隐约约还记得去年砌下的旧巢,但又不能确认。燕子打量了多少屋檐雕龙描凤的殷实之家,想找出去年旧巢,但它们最终还是飞来飞去,迟疑彷徨,找不到一个栖息或再筑新巢的地方。谁人能够了解燕子春去秋来那年年岁岁都萦绕在心头如“丝魂絮影”般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那漂泊与孤寂的燕子呵,前身理应是那一片片凋谢飘零的“落红残粉”。燕子迟疑彷徨,但它们相濡以沫,态度亲昵。它们不停地呢喃,似乎在交换着意见,又似乎在互倾衷肠。它们恩爱的关关鸣声,又让黄莺鸟听得那么专注。燕子虽然恩爱,但它们栖移不定的漂泊生涯,毕竟比不上那日日在水池画栏傍双栖双眠的鸳鸯来得宁静、温馨。
张惠言出生于常州武进县一个世代为儒然科考不彰的清寒家庭,四岁时父亲就病卒,其母将他含辛茹苦教养而成。惠言回忆其早年孤苦生活时描述道:“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餮,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也?吾与尔姊尔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茗柯文编.先妣事略》)。从十四岁开始就外出教授为生,其间两次在安徽歙县金榜家设帐授徒,泄留时间最为长久。二十六岁至三十九岁时又七上京师应进士试。在张惠言四十二岁的生命历程里,约四分之三的时间身居异乡,为糊口而漂泊四方。所以惠言一生饱尝抛妻离子的别离之苦,也屡受寂寞孤苦的煎熬。此词就借咏燕,委婉且淋漓尽致地抒写他身处异乡时那种寂寞难耐的孤苦感,那种漂泊四方时压抑在心头的感伤,那种茕茕孓立时对亲人与故乡不可遏止的思念。词中“满城社雨,又唤起无家,一年新恨”,“前身应是,一片落红残粉”,“输于池上鸳鸯,日日阑前双暝”等语,既是惠言对浪迹天涯燕子的拟人化描摹,更是他此时此刻孤苦、感伤、思念且又有几分怨懑心态的真实反映。张惠言《双双燕》词所反映出来的苦寒人生遭遇,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传统社会中诸多为生计、为功名奔走四方、萍飘天涯的“寒士”们孤苦生涯的真切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