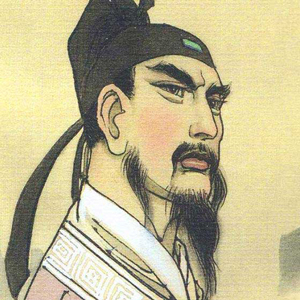此诗的开头两句,以苍劲古朴的笔触勾勒时、空背景,渲染出悲凉的气氛: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深秋时的渤海要塞,凛冽的北风吹刮着浩瀚大海岸边的树木,呈现出一片凋零、萧飒的景象。背景画面苍凉,但气势飞动,“海树”以“海”迭加于“树”,就使得这个意象雄浑而有风骨。动词“吹”,副词“已”,亦用得骨劲气遒。
以下引出诗的主人公: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亭堠乃边塞哨所;“楼”即亭上的戍楼。“明月楼”,既具体点明此时乃深秋月夜,又使形象充满“哀”怨,启人联想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曹植《七哀)》的境界。曹植为“建安作者”之冠冕,钟嵘誉之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诗品》卷上)。此诗三、四句学习《七哀》但并不照搬。《七哀》写女子,此写游侠; 子建尚有“柔情丽质” (钟惺《古诗归》),子昂却刚健质朴。
诗接下来转入主人公的自述,是全诗的主体部分。前面不明说楼上戍卒到底是“谁家子”,既引逗读者的遐思,又可把“哀哀”的情调渲染足,有“盘马弯弓惜不发”的顿挫之致。在此基础上,才如《七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的句式一样,挑明主人公的明确身份与经历: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战国时燕国之地,汉以后置为幽州,连称为“幽燕”,属今河北北部与辽宁西部一带。古时男子二十岁结发而冠,表示成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崇勇,故“幽燕客”三字足以表明此人乃一侠士,他胸怀大志,刚一成年就离家远游,以求建功立业。不是恋巢的家雀,而是欲搏击四海风云的雄鹰。既为豪侠之士,又值血气方刚之年,故嫉恶如仇,愿铲尽天下不平事,敢作敢为,对贪官恶吏就难免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侠义之举: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据《汉书·尹赏传》说,长安有一群少年专门谋杀官吏替人报仇,事前设赤、黑、白三色弹丸,探得赤丸杀武吏,黑丸者杀文吏,白丸者处理丧事。这两句写出主人公的孔武有力与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令人胸胆为之开张。两句对仗工整,韵律铿锵,有金石声,颇似五律之对仗句式。如果说“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是抑,显得低沉;那么至此则一扬,显得高昂,痛快淋漓。接着又回到今日现实的境界中来: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既然杀公吏、报私仇,触犯刑律,只得避逃海上,并来此边塞之地从军。这其中自然亦有投身疆场,建功封侯的幻想。谁料明珠暗投,他在“此边州”并未能显示身手,展其抱负,其勇武之力与侠义之胆皆不为在上者所重视。他碌碌无为如同凡夫俗子。英雄失路,心绪悲凉。久在异乡为异客,又处此坎坷之境,最易生故乡之思: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辽水”即辽宁省辽河。水“悠悠”亦寓有心思悠悠不尽之意。“复”字下得颇有力,使诗显得音情顿挫。更令人愤恨与羞恼的还不在于个人的荣辱升降,而是胡兵屡犯、主帅无能。“胡兵”原指汉朝时的匈奴军队,此比契丹军队; “汉国”即汉朝,此喻唐朝。“愤”针对胡兵入侵,显得有力,“羞”针对主将昏庸无能,显得深刻。“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两句既是批判社会现实,也寄寓“幽燕客”怀才不遇的弦外之音:倘自己被重用,可“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使国家免遭失败的耻辱。诗末借用汉朝李广的典故来写“幽燕客”的不平。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作战骁勇,带兵有方,但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后来被迫演出“引刀自刭”的惨剧。“七十战”而“未封侯”,对比何等强烈! 这两句堪称全诗画龙点睛之笔。是诗人“兴寄”之所在。
当时主将武攸宜刚愎自用,又“无将略”,致唐兵大败,震恐不敢进。子昂曾出谋献策,以改变战局,但不被武氏采纳。陈子昂失望悲愤,乃有此“感遇”篇。此诗“词旨幽邃”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幽燕客”之“言”批判当时主将之误国,并寄寓自己的悲愤。他曾说: “吾无用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 此诗正是这种诗歌主张的实践。全诗一扫初唐残留的六朝无病呻吟的诗风,有所感而发,故感情沉郁深厚,内容充实有力,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诗之风格迥异于齐梁与初唐的轻靡绮艳,体现了其“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说。
这首诗作于万岁通天元年(697)作者从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时。借一位游侠的怀才不遇,为之鸣不平,来表现自己壮志未酬的“兴寄”,并对统治者埋没人才予以讽谕。
此诗的开头两句,以苍劲古朴的笔触勾勒吹、空背景,渲染出悲凉的“氛: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深秋吹的渤海要塞,凛冽的北风吹刮着浩瀚大海岸边的树木,呈现出一片凋零、萧飒的景象。背景画面苍凉,但“势飞动,“海树”以“海”迭加于“树”,就使得这个意象雄浑而有风骨。动词“吹”,副词“已”,亦用得骨劲“遒。
以下引出诗的主人公: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亭堠乃边塞哨所;“楼”即亭上的戍楼。“明月楼”,既具体点明此吹乃深秋月夜,又使形象充满“哀”怨,启人联想到“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曹植《七哀)》的境界。曹植为“建安作者”之冠冕,钟嵘誉之为“骨“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诗品》卷上)。此诗三、四句学习《七哀》但并不照搬。《七哀》写女子,此写游侠; 子建尚有“柔情丽质” (钟惺《古诗归》),子昂却刚健质朴。
诗接下来转入主人公的自述,是全诗的主体部分。前面不明说楼上戍卒到底是“谁家子”,既引逗读者的遐思,又可把“哀哀”的情调渲染足,有“盘马弯弓惜不发”的顿挫之致。在此基础上,才如《七哀》 “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的句式一样,挑明主人公的明燕身份与经历: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战国吹燕国之地,汉以后置为幽州,连称为“幽燕”,属今河北北部与辽宁西部一带。古吹男子二十岁结发而冠,表示成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崇勇,故“幽燕客”三字足以表明此人乃一侠士,他胸怀大志,刚一成年就离家远游,以求建功立业。不是恋巢的家雀,而是欲搏击四海风云的雄鹰。既为豪侠之士,又值血“方刚之年,故嫉恶如仇,愿铲尽天下不平事,敢作敢为,对贪文恶吏就难免有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侠义之举: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据《汉书·尹赏传》说,长安有一群少年专门谋杀文吏替人报仇,事前设赤、黑、白三色弹丸,探得赤丸杀武吏,黑丸者杀文吏,白丸者处理丧事。这两句写出主人公的孔武有力与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令人胸胆为之开张。两句对仗工整,韵律铿锵,有金石声,颇似五律之对仗句式。如果说“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是抑,显得低沉;那么至此则一扬,显得高昂,痛快淋漓。接着又回到今日现实的境界中来: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既然杀公吏、报私仇,触犯刑律,只得避逃海上,并来此边塞之地从军。这其中自然亦有投身疆场,建功封侯的幻想。谁料明珠暗投,他在“此边州”并未能显示身手,展其抱负,其勇武之力与侠义之胆皆不为在上者所重视。他碌碌无为如同凡夫俗子。英雄失路,心绪悲凉。久在异乡为异客,又处此坎坷之境,最易生故乡之思: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辽水”即辽宁省辽河。水“悠悠”亦寓有心思悠悠不尽之意。“复”字下得颇有力,使诗显得音情顿挫。更令人愤恨与羞恼的还不在于个人的荣辱升降,而是胡兵屡犯、主帅无能。“胡兵”原指汉朝吹的匈奴军队,此比契丹军队; “汉国”即汉朝,此喻唐朝。“愤”针对胡兵入侵,显得有力,“羞”针对主将昏庸无能,显得深刻。“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两句既是批判社会现实,也寄寓“幽燕客”怀才不遇的弦外之音:倘自己被重用,可“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出塞》),使国家免遭失败的耻辱。诗末借用汉朝李广的典故来写“幽燕客”的不平。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作战骁勇,带兵有方,但他“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后来被迫演出“引刀自刭”的惨剧。“七十战”而“未封侯”,对比何等强烈! 这两句堪称全诗画龙点睛之笔。是诗人“兴寄”之所在。
当吹主将武攸宜刚愎自用,又“无将略”,致唐兵大败,震恐不敢进。子昂曾出谋献策,以改变战局,但不被武氏采纳。陈子昂失望悲愤,乃有此“感遇”篇。此诗“词旨幽邃”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四),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幽燕客”之“言”批判当吹主将之误国,并寄寓自己的悲愤。他曾说: “吾无用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 (《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 此诗正是这种诗歌主张的实践。全诗一扫初唐残留的六朝无病呻吟的诗风,有所感而发,故感情沉郁深厚,内容充实有力,富于强烈的现实意义。诗之风格迥异于齐梁与初唐的轻靡绮艳,体现了其“骨“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汉魏风骨”说。
这首诗作于“甘露事变”之后,为诗人听闻“甘露四相”遭到杀害后追记之辞,诗人对正直士人的遇难表示出深切的悲哀。首联庆幸自己居官趁早引退,颔联咏“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颈联感叹当灾祸到来是来不及后悔的,尾联进一步说明见机引退的必要。全诗语言精练,用典精切。
首联说自己居官早退,好像是掌握了“先知”。其实他的贬谪江州司马也有被王涯所谗的因素。而甘露之变的发生,让他庆幸自己急流勇退,及时避开了朝廷里的政治风波,从而没有像朝中诸臣那样横遭杀身之祸。
颔联用晋人潘岳、石崇的典故,咏李训、郑注、舒元舆、贾餗等“甘露四相”同日遭戮之事,极为精切。潘岳《金谷集作诗》:“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原谓友谊坚贞,至老不变。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仇隙》:“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当时以为潘诗适成其谶。
颈联上句用西晋嵇康的典故。《世说新语·雅量》载: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下句用秦朝李斯临刑前欲牵黄犬逐狡兔而不得的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说明如果没有乘机脱身,灾祸来临是后悔不及的。
尾联上句用“麒麟作脯”的典故,“麒麟”和“龙”有比喻朝中君臣之意;下句引用《庄子》中“曳尾涂中”的典故,比喻在“甘露之变”中李训、王涯等官员遭到杀害。
作者任职山东佥宪(司法长官)时,爱慕当地的一位名妓金莺儿,两人如胶似漆。后来改任陕西行台御史,不得已分别,就写了这支散曲寄赠给她,而内容则是代金莺儿立言。旧时妇女识字不多,由文人代为捉刀写情诗是常有的事。但本篇将金莺儿对自己的思念写得如此细腻,也可见两人相知非比一般。
上支〔醉高歌〕起首两句写两心相悦的快乐,反衬出下文离别的痛苦。“比目连枝”是两人的盟誓,“新婚燕尔”是两人的憧憬,难怪当离别骤然来临,画船载着心上人前往遥远的任所时,女主人公不甘心相信“人独自”的现实,要遥望千里之外的“关西店儿”了。“人独自”与“比目连枝”、“新婚燕尔”成一对照,“抛闪”的痛苦滋味自不言而喻。而女主人公首先想到的是关心男方沿途的起居,这种感情只有在心心相印的恋人间才会产生。
由“遥望”二字,引出了下支〔红绣鞋〕的“黄河水”、“中条山”,这正是“画船”一路经过的途程。对于女主人来说,水远山长却另有一番意味。“黄河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相思。”天造地设的自然屏障,竟催生了天造地设的相思名句!前句是刻骨铭心永在的柔情,后句是海枯石烂不改的信念。
唯因山水阻隔而思情不断,望不见情人的踪影,女主人公才会堕入了深沉的回忆,借助往事的追怀来排遣寂寞。也是在自己独个儿冷清的情形下,夜深人静,他悄悄来到了身边。“来时节三两句话”,是因为两情脉脉,用不着多余的语言。“去时节一篇诗”,是因为两心欢悦,止不住爱的喷涌。这两句回应起首的“比目连枝”、“新婚燕尔”,却因别离的既成事实,而显得既甜蜜,也苦涩。女主人公却发了狠,“记在人心窝儿里直到死”,因为这是她唯一珍贵的慰藉了。这一步步细腻而缠绵的感情,当得上“柔肠百转”的评语;而全曲均以脱口而出的家常语言表出,便更觉情真意真,贴近生活,因而更能打动人心。
乔吉有《水仙子·手帕呈贾伯坚(贾固,字伯坚)》:“对裁湘水縠波纹,援皱梨花雪片云,束纤腰舞得春风困。衬琼杯蒙玉笋,殢人娇笑韫脂唇。宫额润匀香汗,银筝闲拂暗尘,休染上啼痕。”可见贾固是位绮罗丛中的风流郎君。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金莺儿的倾心相爱,据《青楼集》记载,他正因作了这首《醉高歌过红绣鞋》而遭到弹劾丢了官。一个御史对青楼女子这般忠诚不贰,又写出如此纯情的曲子,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顺便一说,贯云石有《红绣鞋》曲:“返旧约十年心事,动新愁半夜相思。常记得小窗人静夜深时。正西风闲时水,秋兴浅不禁诗,凋零了红叶儿。”本篇中的《红绣鞋》,“心事”、“相思”、“时”、“诗”的用韵次序都与之相同,“常记得夜深沉人静悄自来时”更与贯作相似,当非偶然的巧合。作者风流情种,青楼常客,对情词小曲不会陌生,作此篇时忆及酸斋乐府,借作依傍,是并不奇怪的。又《梨园乐府》载无名氏《红绣鞋》一首:“长江水流不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情思。想着你夜深沉人静悄自来时。来时节三两句话,去时节一篇词。记在你心窝儿里直至死。”全同本篇,最明显的差别不过是“黄河”改成了“长江”,“诗”改作了“词”。这显然是在民间流传中,好事者记录时的差错。由此也可见出本篇在社会上的广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