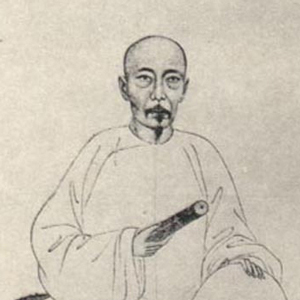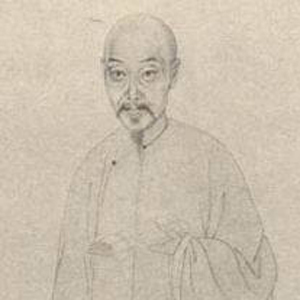“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汉乐府民歌的特色,这一特色也充分地体现在这首《满歌行》中。用铺陈的手法,通过对诗人自己的遭遇、志趣、思想、认识的叙述,剖白、刻画了抒情主人公这个远祸晋身、向往隐逸的封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全诗共分为五解。开头一直到“谁当我知”为第一解,写自己乱世逢忧不被人理解的遭遇。踏入仕途没多久,便遇上乱离的世道。家国、自身、前途抱负,各种忧患一起向自己袭来。孤独痛苦,就如同难以治愈的疾病无法摆脱,无人理解。诗人在铺叙的过程中,抓住表现主人公心理活动的细节描写,“遥望极辰,天晓月移”,对深刻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解自“戚戚多思虑”到“守此末荣”,倾吐辞官归隐、躬耕陇亩之志。动荡的时局,多变的官场,使诗人对“祸福无形”的仕途生涯充满忧虑和恐惧,以致使他“耿耿殊不宁”,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担惊受怕,就为那微爵薄禄,有何不可割舍呢?他要像古代许由一类隐士一样淡泊功名,躬耕陇亩,满足平日愿望,以此来求得内心的平静。
从“暮秋烈风”到“劳心可言”为第三解,写归隐前的思想顾虑。“暮秋烈风”“昔蹈沧海”,诗人借助比喻、象征的手法,形象含蓄地表现归隐时的顾虑。正值暮秋烈风天气,漂泊大海上,心潮滚滚,犹如汹涌起伏的海涛一样难以平静。这种艺术手法,令人联想,耐人寻味。“揽衣瞻夜,北斗阑干”,既是对诗人动作的具体描写,又是对诗人心理活动的剖析。诗人内心忧虑,夜不能寐,揽衣出户星斗。银河照着诗人,使他辞官归隐,不再忧虑。奉养父母双亲,使心劳累何待言。
第四解自“穷达天为”到“名垂千秋”,集中抒发安贫乐道的思想感情。诗人面对战祸遍地的社会无能为力,但却不甘心,又要达到内心平衡,只好借助于“天命”,再加上颇具“圣名”的先行者,为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寻找堂皇的理由。他认为一个人处境的穷困和通达是由天决定的,因此明白穷达之理的“智者”就不会因处境困顿而犯愁。虽知躬耕之劳辛苦,但“身虽多为”,而“心自少忧”。“安贫乐道”以下六句,明确指出“安贫乐道”的主张,并且把庄周和子遐奉为榜样,要像他们那样处世。
第五解从“饮酒歌舞”至篇末,写如何处世,才能长寿。这一解,诗人主要以议论的方式,抒写了人生在世如“凿石见火”,应及时行乐,修身养性,以保长寿,抒写了消极悲观的远祸晋身的处世态度。
强烈的现实主义内容,对人生态度自然直率的表达是这首诗的一大特色。语言精练,富有理趣。无意塑造形象,但一个封建士大夫、忠臣、孝子、隐士的形象却跃然纸上。
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两军厮杀的观战记,倏来忽往,更显出一种速写式的精炼与激烈。人手的角度也颇为新颖,是从一名牧人在无意中的遭遇和目击来展开全篇。和平的牧野转眼间变成了血肉纷飞的战场,这就更增添了战争的残酷意味。曲中插入的两组感受和评论:“俺牛羊散失,你可甚人马平安”,“把一座介丘县,生纽做枉死城,却翻做鬼门关”,更是老辣当行。这支散曲绘声绘色,情景栩栩如生,令人过目难忘。
起笔从“牛羊”开始。牛羊感觉敏锐,觉察到情况异常,发生了骚动。牧人起初并未意识到危险,“犹恐”说明他全副心思都集中在牛羊的失常上,“子索”、“不住”,显示出他竭力控制牧群的手忙脚乱。“紧遮拦”的努力多少奏了效,这才发现了牲畜受惊的外界原因——“枪刀军马无住岸”。这一起笔细腻而真实,借机交代了对阵两军的突然出现与渐次逼近。由牛羊的惊散渐而写到牧人的惊走,战争的残酷气息便先已笼罩全篇。作者安排牧人由“走”到“听”,“听罢”再探出草丛爬上高阜“偷睛看”,既渲染出一种紧张的氛围,又省略了两军交战的最初接触,使牧人作壁上观,一下子就目击到了短兵相接的关键景象。
“吸力力振动地户天关”是杀声,更是一股杀气,这是从大处着笔。“那枪”等三句,则细绘了刀来枪往的三组具体镜头。“忽地”、“亨地”、“扑地”都是象声,而“忽地”兼有突然意,“亨(呼)地”兼有沉重意,“扑地”兼有扑倒意,加上“刺”、“掘”、“抢”等形象的动词,使激烈的战况显得惊心动魄。对于像牧人这样的平民百姓来说,这些血淋淋的景象是终生难忘的,因而他在惊魂未定中的现场感受,也就更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与认同。
最后一支[采茶歌]中,胜负已成定局,于是败军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而胜方则毫不留情地乘势追击。末三句便表现了追赶的情形。“歪刺刺”在此是象声词,而三字又有东倒西歪的本义,作者有意用上,多少含有讽刺愤蔑的微意。特意表出“饮牛湾”,以及“红尘遮望眼”、“红叶落空山”的景色描写,都是在同时强调战争对宁静生活的骚扰与破坏。至此我们更可理解作者安排牧人为曲中主角的用心,正是为了表现无辜百姓对战乱带来惊恐威胁的愤怒与控诉。
这支散曲绘声绘色,情景栩栩如生,令人过目难忘。语言上带有民间文学的强烈特色,如运用大量的口语、象声词,运用顶真手法,使用尖新生动的对仗等等。尤其是曲中插入的两组感受和评论:“俺牛羊散失,你可甚人马平安”,“把一座介丘县,生纽做枉死城,却翻做鬼门关”,更是老辣当行。前者利用“牛羊散失”与“人马平安”的字面对仗,化常语为尖巧;后者则搬用说唱中的习语,恰合“鏖兵”的题面与本质。无论从题材、语言及表现手法来说,这支无名氏的作品,在元散曲中都是别具一格、令人刮目相看的。
“翩与”二句,是写北行时寂寞凄凉的情怀。翩然和回归北方的鸿雁共同北行。登山临水,据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这里借用此句来表达诗人的离乡之愁。
“江南”二句就真实地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痴情。“江南”句是古诗名句,据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里借用此句点明了北上的时间,正是江南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样美好的季节离开故里北上,留恋之情更加难舍难分。
在交待了离乡的时间以后,“五夜”二句又进一步交待了北行的原因。“五夜”即五更,这里指通宵。“伏枥”出自曹操《步出夏门行》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左计,失策。躬耕,亲自耕作。这两句的意思是:通宵不眠,我象伏枥的老马壮心不已;没有亲自操作于田野,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了。这就是说,我还有壮志未酬,所以还不能归隐田园。那么,他的壮志是什么呢? 最后两句做了交待。《两当轩集》前言说:“黄景仁的诗歌主要是反映个人身世的穷愁不遇,抒发寂寞凄凉的情怀为多,虽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但有些作品的基调较低沉。”黄景仁对自己诗歌的这些不足之处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自嫌诗少幽燕气”,也就是说缺乏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所以才“故作冰天跃马行”,为了转变“少幽燕气”的诗风,诗人甘愿从草长莺飞的江南到冰天雪地的北方跃马前行。
这首诗巧用比兴,含意深远。语言明快晓畅,而又妥贴传神,富有表现力。“故作冰天跃马行”一句含蓄而隽永,似是在写诗人在冰天雪地中跃马前行,实则是写出诗人希望自己的诗要有“幽燕气”。向豪壮处发展。全诗不乏佳词警句,含英咀华,耐人寻味。
本首诗细致地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芭蕉画面,并联想到了含情不展的少女的感情与气质,创造了一个别具新意的艺术形象。全诗含蓄凝练,想象丰富,色彩鲜润宜人,情思沁人心脾,韵味悠长,颇具艺术美感。
丰富而优美的联想,往往是诗歌创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咏物诗,诗意的联想更显得重要。钱珝这首《未展芭蕉》就是运用联想的杰作。
首句从未展芭蕉的形状、色泽设喻。由未展芭蕉的形状联想到蜡烛,这并不新颖;“无烟”与“干”也是很平常的形容。值得一提的是“冷烛”、“绿蜡”之喻。蜡烛通常是红亮、温暖的形象,这里却说“绿”、“冷”,不仅造语新颖,而且表达出诗人的独特感受。“绿蜡”给人以翠脂凝绿的美丽联想;“冷烛”一语,则显示出那紧紧卷缩的蕉烛上面似乎笼罩着一层早春的寒意。
“芳心犹卷怯春寒”。卷成烛状的芭蕉,最里一层俗称蕉心。诗人别开生面,赋予它一个美好的名称──芳心。这是巧妙的暗喻:把未展芭蕉比成芳心未展的少女。从表面看,和首句“冷烛”、“绿蜡”之喻似乎脱榫,其实,无论从 形象上、意念上,两句都是一脉相通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有心惜别”的蜡烛本来就可用以形容多情的少女,所以蕉心──烛心──芳心的联想原很自然。“绿蜡”一语所显示的翠脂凝绿、亭亭玉立的形象,也常象征着美丽的女性。
在诗人想象中,这在料峭春寒中卷缩着“芳心”的芭蕉,仿佛是一位含情脉脉的少女,由于寒意袭人的环境的束缚,只能暂时把自己的情怀隐藏在心底。如果说,上一句还只是以物喻物,从未展芭蕉的外在形状、色泽上进行描摹刻画,求其形似;那么这一句则通过诗意的想象与联想,把未展芭蕉人格化了,达到了人、物浑然一体的神似境界。句中的“犹”字、“怯”字,都极见用意。“犹”字不只明写当时的“芳心未展”,而且暗寓将来的充分舒展,与末句的“会被东风暗拆”遥相呼应。“怯”字不仅生动地描绘出未展芭蕉在早春寒意包围中卷缩不舒的形状和柔弱轻盈的身姿,而且写出了它的感觉与感情,而诗人的细意体贴、深切同情也自然流注于笔端。
“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芳心犹卷的芭蕉有如一卷书札,真不知她内心蕴藏了多少心事。风儿会捷足先登知道芭蕉满腹心思。
后两句却又另设比喻。古代的书札卷成圆筒形,与未展芭蕉相似,所以这里把未展芭蕉比喻未拆封的书札。从第二句以芳心未展的少女设喻过渡到这一句以缄封的书札设喻,似乎又不相连属,但读时有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这奥妙就在“藏”字上。书札紧紧封缄着,它的内容——写信者的一片芳心就深藏在里面,好像不愿意让人知道它的奥秘。这和上句的“芳心”犹卷在意念上完全相通,不过上句侧重于表现客观环境的束缚,这一句则侧重于表现主观上的隐藏不露。未曾舒展的少女情怀和包蕴着深情的少女书札,本来就很容易引起由此及彼的联想。但后两句并非用另一比喻简单地重复第二句的内容,而是通过“藏何事”的设问和“会被东风暗拆看”的遥想,展示了新的意境,抒发了更美好的情思。
在诗人的想象中,这未展芭蕉像是珍藏着,美好情愫的密封的的少女书札,严守着内心的秘密。随着寒气的消逝,芳春的到来,和煦的东风总会暗暗拆开书札,使美好的情愫呈露在无边的春色之中。既然如此,又何必深藏内心的奥秘,不主动的坦露情怀,迎接东风,欢呼春天的到来呢?这后一层意思,诗人并没有点明,读者却不难领会。句中的“会”字,让人感觉到芭蕉由于怯于春寒不展,到被东风吹开,是顺乎自然规律的;而“暗”字则精细的显示出这一过程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这两个词语,对深化诗的意境有重要的作用。
诗意的想象与联想,归根结蒂还是来源于对生活的细心体察和深切体验。如果钱珝对生活中受到环境束缚、心灵上受到禁锢的少女缺乏了解与同情,那么他是无论如何不会产生上面那一系列诗意的联想的,也绝不会从单调的未展芭蕉身上发现含情不展的少女的感情与气质的。
词作上片写金陵的地理形势。开首即以赞美的口吻称之“佳丽地”。“南朝盛事”,点出南京古来即有盛名,扣题。起二句为总括。“南朝”,指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到580年陈亡,建都建康(金陵)的宋、齐、梁、陈等朝代。以“谁记”提起,加以强调:“南朝盛事”已随流水逝去,人们早已将它遗忘了。
“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可是,金陵的山川形胜却依然如故。这两句主要写山,水为陪衬,描绘出金陵独特的地理形势一群山环抱,耸起的山峰,隔江对峙;且以美人头上的“髻鬟”形容山峦,以“清字形容江水,不仅形象,而且显示出金陵山清水秀的美好景色。如今,旧时王朝的都城,却“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当年“豪华竞逐”的金陵,而如今却是座“孤城”,潮水的拍击声正反衬出环境的寂静冷漠,天际的风帆给人一种空旷落寞之感。词人通过景物描绘,极力渲染这些历史遗迹的冷落,正在被遗忘,与上文“谁记”相应,抒发了深沉的怀古之情。
词作中片写金陵的古迹。开首以景出,“断崖树,犹倒倚”,着一“犹”宇,强调景色依然,使眼前实景,带上历史色彩,下面又追加一句“莫愁艇子曾系”。这里化用了古乐府《莫愁乐》:“莫愁在何处?住在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点出古迹。接下继续写景,“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郁苍苍”,谓云雾很浓,望去一片苍青色,埋没了半边城的营垒。结尾二句点明时间是“夜深”,地点在“赏心亭”,即夜深时分,词人仍站在赏心亭上,观览莫愁湖和秦淮河的景色,不禁发出景物依然而人事已非的喟叹。这两句起到束上启下的作用,即上面所描绘的景色,皆是由此观览到的,又引出下片怀古的感慨。
词作下片,写眼前景物。“酒旗戏鼓甚处市”,这是词人眼前见到的景色:酒楼、戏馆,一派热闹景色,不禁发出“甚处市”问语,这是何处的繁华市面呢?前面两片所写多是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这里则写连景物也变了。当然,酒楼、戏馆并非纯自然景色,而是包含人事在内的。这情况引起词人的猜想。“想依稀、王谢邻里。”是说这些酒楼戏馆所在地,仿佛是当年王、谢两家比邻而居的乌衣巷,也就是说,贵族住的乌衣巷如今换了主人。至此,词人不禁产生人世沧桑之感,于是结尾发出“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兴亡慨叹。燕子是不知人事变迁的,依然飞进往年栖息过的高门大宅,而今已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房舍。然而词人看到夕阳余晖中成对的燕子,却认为它们有知,且正在议论兴亡大事!这当然是词人内心的兴亡之感赋予了燕子而已。这片从眼前景物引起对金陵古都朝代更替的无限兴亡之感,从而表达出咏史的题意。
本篇为咏金陵旧迹,感慨历史兴亡的名作。上片总写金陵形胜,境界旷远,雄壮中蕴含落寞。“寂寞”二字透出历史变迁,人亡物移,故国繁荣与孤城幽寂的荒凉。中片糅合当地传说,扣紧金陵景观抒发物是人非之感,“断崖”“旧踪”“雾沉”等为景物涂上了一种苍茫的色调。下片以何处寻得当年“酒旗戏鼓”的繁华街市的感叹发端,侧重写“王谢邻里”的豪门旧迹难以寻觅,只可依稀辨识,抒发人世沧桑之思。燕子相对说兴亡于斜阳之中,意象极巧,感伤殊深。全词强化了景物描写的清峭、冷寂而又悲壮、苍凉之情韵,境界开阔,内蕴深远。
宋代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一些怀古名篇: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至周邦彦这首《西河·佳丽地》;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到姜夔的《扬州慢》,可以说各有千秋,难分轩轾。这些作品,有的是以突兀见长,有的是以绵密取胜;介于突兀和绵密之间的是这首《西河》。它从时间上说是断续交织,从空间上来说,是疏密相间。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上片,只是泼墨画似的写了“江山如画”,下片集中写了周瑜,一气贯注,如同骏马驻坡,纯属粗线条的勾勒。姜夔的《扬州慢》,侧重于主观感受的深微描绘。笔墨之间,隐约可以听到凄清的号角声和感受到随着号角声传来的寒意而伴着寒意的角声,偏又是在一个兵荒马乱后的萧条古城中吹彻。这些都说明作者牢牢扣紧了寓有深意的景物,进行密密层层的渲染。至于周邦彦的这首词,似乎介于泼墨写意与工笔细描之间。如:词的上片以疏为主。词人放眼江山,对作为“佳丽地”的“故国”金陵做了一个全面的鸟瞰,描绘了江上有山峰夹峙和江心有怒涛汹涌的雄伟形势。第二部分以密为主。在上片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勾勒:从前面围绕“故国”的山峰,引出了后面的“断崖树”,以至想象中的“莫愁艇子”;从前面的“清江”,引出后面的“淮水”;再从前面的“孤城”,引出后面的雾中“半垒”和月下“女墙”。这就好比电影镜头,缓缓而来的不再是远景全景,而是中景和近景了。下片,画面突出的是特写镜头:一帧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呢喃图。小小飞禽的对话,可以说刻画入微,密而又密。“相对”,可能指燕子与燕子相对,也可能指诗人与燕子相对,完全可以听凭读者用想象来补充。尽管它们的呢喃本无深意,然而在诗人听来看来,却为它们的“不知何世”而倍增兴亡之感。“疏”利于“写大景”(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写出高情远意;“密”利于画龙点晴,写出“小景”,写出事物的不同于一般的特征。杰出的怀古词一般都是能做到“大”“小”结合、“疏”“密”相兼的,这首《西河》更为突出。总体来说,周邦彦这首怀古词,艺术技巧极其精湛,比起他的大量送别、怀人之作,的确别具一格;特别是寓悲壮情怀于空旷境界之中,并使壮美和优美相结合,确是怀古词中一篇别具匠心的佳作。
此外,周邦彦的《西河》与其他怀古之作不同的是,并不正面触及巨大的历史事变,不着丝毫议论,而只是通过有韵味的情景铺写,形象地抒发作者的沧桑之感,使人触景生情,见微知著。怀古之作,总要描写标志着沧桑之变的景物,王安石的怀古是从当前的“千里澄江”和“彩舟云淡”——故国的风景宜人,过渡到昔日的“豪华竞逐”。苏轼的怀古则从眼底的“大江东去”,写到古代有关三国赤壁战时的“多少豪杰”,再联想到当前自己的壮志成虚,年华已逝。但这些都不像周邦彦词通篇写景,以景物描绘的逶迤曲折为线索,从头到尾把一切情语完全熔铸于景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