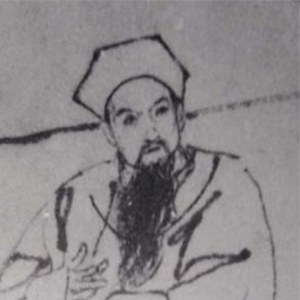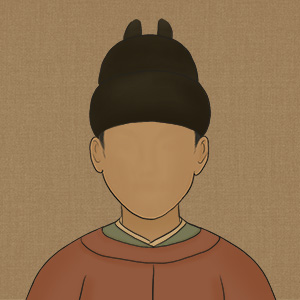译文及注释
译文
陆游寄居他乡,获得两间房子,屋子狭窄而深邃,形状宛如小舟,所以将屋子命名为“烟艇”。客人说:“真奇怪啊,屋不是船,就像船不是屋,可以认为它们相似吗?船本来有高大明亮,内部幽深华美甚至胜过宫室的就被称作屋,这样可不可以呢?”
陆先生回答:“不是这样的!新丰不是楚地原来的丰邑,虎贲卫士不是中郎将。这样的道理谁不知道?心里真正喜欢但却得不到,得到一个粗略相似的,就会以心中所喜欢的来为它命名。依照这样的名字考察实际所指的东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又有什么错呢?我年轻时就多病,自己想着不能在当世施展微小的作用,所以曾有所感慨产生了归隐江湖的念头,但因为迫于现实的饥饿、寒冷,又有妻儿拖累,我就只能把自己的志趣寄托在烟波洲岛之间,一日也不曾忘掉。假使再过几年,儿子们能够胜任耕种的劳动,女儿们能够胜任织布的劳动,衣食勉强不缺,这样以后得到一叶小舟,就砍砍柴、钓钓鱼、卖卖菱角和芡实,乘着小船进入吴淞江,逆流而上到严陵濑这个地方,游历石门涧、沃洲之后再回来,把小船停靠在苍翠的山峦下,醉了就披散头发击舷唱唱吴歌,难道不快乐吗?虽然高官厚禄和一艘小船相比,穷困与显达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然而这两者都是身外之物。我知道很多的俸禄不可强求,就不能不念念不忘一叶之舟,那果真能求得吗?归隐山水的意愿使我的胸怀浩大空旷,可收纳云霞日月的雄伟壮观,能包揽雷霆风雨的奇异变幻,即使居住在狭小的房屋,而常觉得像顺流行船,转瞬之间游于千里之外,这样看来,谁能确定这屋子真的不是烟波上一艘小船呢?”
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一日作此记。
注释
陆子:陆游自称。
寓居:陆游当时在临安租房居住,因此称为寓居。
楹:计算房屋的单位,一间为一楹。
高明奥丽:高敞明亮,宏深壮丽。逾:超过。
新丰非楚:新丰并不是楚地的丰县。汉高祖刘邦本是楚地丰县(在今江苏西北)人,称帝后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其父思念家乡故人,刘邦便在故秦骊邑仿丰地街巷筑城,建新丰,并把丰县的故人搬来,以取悦其父。新丰故城在今陕西临潼东。
虎贲非中郎:犹言那勇士不是中郎将蔡邕。虎贲,勇士之称。东汉名士蔡邕曾任中郎将,后为王允所杀。他的朋友孔融看到一虎贲士貌似蔡邕,酒酣,引与同座,并说:“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型。”(见《后汉书·孔融传》)贲,通“奔”。
粗得其似:大致相像。粗,粗略。
因名以课实:依据名称去考求事实。
江湖之思:隐居的打算。江湖,江河湖海之省称,一般用以指隐居生活。
累劫:屡次遭到灾祸。
杳霭:烟云隐现的样子。
胜:胜任。
鉏:同“锄”。
荻:多年生草本植物,秆可编织席箔等。
芰:菱角。
芡:一名“鸡头”,种子称“芡实”,均可供食用。
松陵:地名,在浙江绍兴、桐庐间。
严濑:指严子陵隐居之处,在今浙江桐庐南。濑,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
石门:山名,在浙江青田西。
沃洲:山名,在浙江嵊县。
玉笥:山名,会稽山的主峰,在浙江绍兴东南。
万锺之禄:古代高级官员的俸禄。锺,古代计量单位,六斛四斗为一锺。
眷眷:依恋不舍的样子。
浩然廓然:宽阔广大的样子。
容膝之室:室小仅能容双膝,极言其狭小。
放棹:指放船。棹,摇船的用具,这里指船。
瞬息:一眨眼一呼吸之间,谓时问短促。
这篇文章由取名的奇特而引起——一位客人代读者向作者提出了这个疑问: “屋是屋,舟是舟;屋之非舟,就像舟之非屋。若您认为二者有相似之处,所以把小屋取名为‘烟艇’;那么,有些舟船的高大明亮、深邃富丽甚至超过了宫室,您难道也把这些舟船称之为‘屋’吗?”对此,就引发了作者一大通的议论,而其主旨即在于下面这句: “意所诚好而不得焉,粗得其似,则名之矣。”也就是说,作者虽然身困于小屋之中,但心所向往的却是“烟艇”;现在二者既有某些相似,那就何不借给小屋取名为“烟艇”,以之寄托自己的志趣,填补“求而不得”的心理缺憾?文章就用“逗人悬念”的方法开头,然后结出此文的主题: “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即是: 身居陋室而心怀烟波浩淼的隐逸生活。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烟艇”这个词语实际已成了隐逸生活的“感情象征”。这个“感情象征”的形成,时间很早,其源似乎可以推溯到《史记》中所记载的范蠡,他于辅助勾践灭吴之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就隐约出现了“烟艇”的“雏形”。后来,有许许多多文人又进一步对之“加工”,就形成了对于“烟艇”的更加生动优美的描绘。举其最常见者,如中唐人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其平生大愿是“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而他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就更为他的“烟艇”生活披上了一层“诗”的美丽外衣。再如苏轼,在他有名的《前赤壁赋》中也出现过如此旷逸的意境: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这里的“一苇”和“一叶扁舟”,实际上也就是“烟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至于陆游本人,他对“烟艇”生活亦即隐逸生活的向往,更可举其《澄怀录》中对朱敦儒隐居生涯的记述为例: “朱希真居嘉禾,与朋辈诣之。闻笛声自烟波起,顷之,棹小舟而至,则与俱归。”请看,朱敦儒放舟于烟波之间,吹短笛而唱渔歌的隐逸生活就是这样逍遥自在,优哉游哉。所以,陆游把自己的小屋命名为“烟艇”,就明显地寄寓着他对这类隐逸生活“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无限企慕之情。对于这种生活理想,他在此文里也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写: “得一叶之舟,伐荻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上严濑,历石门、沃洲,而还泊于玉笥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顾不乐哉!”在这段话中,似乎看到了古代无数高人隐士的身影,也似乎预见了他在晚年所作《鹊桥仙·一竿风月》中所勾画的“自我形象”: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故而,陆游之为小屋取上一个奇特的“烟艇”之名,实有深意存焉。
现在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 陆游当时正值初入仕途之际,又年当身健力壮之龄(三十七岁);照理,一个人产生隐逸之思常是在倦于官场及年晚力衰之时,但现今却提前出现了这种欲求退隐的心理倾向。对此,仍应从此文的字里行间去细求。文中一曰: “予少而多病,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二曰: “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这就提供了两方面的答案: 第一,作者其实早有“用世”之大志(他早在三十二岁所作的《夜读兵书》诗中就说过: “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但因投降派的打击(他三十岁赴礼部试时曾被主考官名列前茅,却为秦桧所黜落),迟迟未能伸展其大才。现今虽在京师任职,然而仍“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所以就自然而产生那种思欲归隐的思想。第二,作者尚有生计之累,于此,也生发了“做官不如回家种田打鱼”的牢骚。故而,陆游之名其小屋为“烟艇”,一方面是表达了自己从中国士大夫传统思想中承传而得的隐逸情趣,另一方面却又可以看作是他怀才不遇、不满现实的愤懑情绪之表露。只有把这两方面综合起来看,始能比较全面与深刻地认识他此时此地的复杂心态。
中国古代文人常会遇到这样的心理矛盾:是“入世”,还是“出世”。是为国家建功立业,还是退隐江湖,做一个高人隐士。在他们看来,这两方面就像“鱼”与“熊掌”那样,都是“我所欲也”却又“不可得兼”。于是,便出现了李商隐那种思欲“调和”或“统一”这二者的诗句: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也就是说: “隐逸江湖”之思,是终身所怀的愿望;不过,真正的归隐,当在干过一番回天转地的大事业、两鬓斑白之后方始心安理得地实行。可惜的是,这种理想除开极少数人(如范蠡)外,几乎都无法做到。因而,陆游在此文中就改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述他那既不能效功于当世又不能真正归隐江湖,既身困于陋屋闲官又强烈心怀故乡田园的苦恼;而如果再深一层挖掘,便可从其“反面”发现: 作者的真正愿望却仍在李商隐的那两句诗中。这样,通过“剥笋抽茧”式的分析,就能透过其表层的翳障而直探其心灵奥区: 此文实际是以旷逸之语来发泄他思欲用世而不能的苦闷——果然,在此文写后不久,陆游便有机会积极投身于当时的抗金北伐战争中去了(先是上书《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主张北伐;后是改调镇江通判,筹画军事);到那时,既不见了他困于“饥寒妻子之累”的倦色,也听不到他“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的喟叹,而只看到一位“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壮岁从戎》)的爱国志士,正奔忙出没于抗金前线……
根据以上分析,此文在写作上的特点,除开其发端的故设悬念、引人好奇之外,主要还在于它的借题发挥和弦外有音。“借题发挥”是指借给小屋取名为“烟艇”来抒发他那“身在魏阙,心存江湖”的隐逸志趣;“弦外有音”又是指它的表面作旷达语而实际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牢骚——作者在他后来回忆这段“百官宅”的生活时,尚有诗曰: “簿书衮衮不少借,怀抱郁郁何由倾?”(《往在都下时与邹德章兵部同居百官宅无日不相》)特别对于这后一点,读者须细心体味,方能察其真谛。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