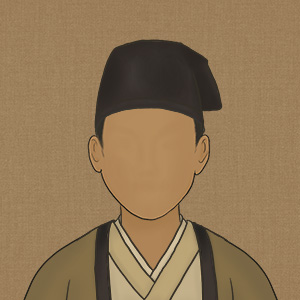此诗以轻松平淡语言作侧面讥刺。前两句叹牡丹价格昂贵而豪家权门挥金如土满不在乎。三句转出,末句直抑。以物比物,写牡丹花与普通蜀葵花差不多。全诗谴责官僚贵族豪华奢侈,任意挥霍民膏民血,同时流露出反对奢靡浪费和对民生疾苦的隐忧关心之情。
“近来无奈社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一开始写出了自己爱花而又无钱买花的矛盾心情。“无奈牡丹何”,即对壮丹无可奈何之意。造成这种状况,作者交待了原因:数十千钱买一颗。用“数十千钱”与“一颗”,在数字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而突出了花的昂贵,其中已经揭示了买花富人的享乐,以及百姓的贫苦。正如白居易写的“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价值竟相当于“五束素”匹帛,“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一丛艳丽的鲜花,竟要花掉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这无可奈何之谙中,蕴藏着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
尽管花的声誉这么高,看来作者无力买花,因而难得赏玩。因为最后他写道: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不较多”,到令天他才分明看到,牡丹花与普通的戎葵差不多。陈标《蜀葵》诗曰:“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案。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闲处只缘多。”农村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乡下姑娘喜欢风仙饼子花,处处人家都有它,城里姑娘喜欢牡丹富贵花,三天一过眼巴巴”,这都说明蜀葵这种花相当普通,品级很低。作者在这里将富贵之花壮丹同普通的蜀葵作一对比,认为这两者差不多。简直是震聋发聩。实际上潜台词是:牡丹花也不过如此,何必不顾民生疾苦,将价格抬得如此昂贵呢?言外之意尖锐讽刺了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的达官贵人。
咏牡丹的诗多写其艳丽不凡和高贵风格,这首诗一反常笔,表现了作者新奇立意。一个‘始”字,“也”字,寄寓了作者深沉的感慨。全诗无一明显论褒贬之词,然而诗人的好恶之情却又得以充分表现,足见诗人手法之妙。
这首诗一共六句,分三层,抒发离家求仕的复杂感情。情与景相间相融,夹以议论。反映汉末一代有抱负青年在乱世中创业,为实现统一安定的能施展才智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虽为知己者死,但死而无怨。这是时代精神的艺术个性化。时代的共性深寓在艺术个性之中,隐现着个性美与人情美的质愫与基因。
诗的开端两句直接入题,写别时景象,暗扣诗题离别后的感伤。“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这两句是触景生情,目及早晨朝霞涌起,由此自然现象,想到浮云升起,飘浮天上,可是到了晚上还是要回到故山,有自己归宿之处。暗示出自己离家外出,如天上浮云一样,飘泊海内。晚年能否落叶归根,重回故土,前途茫然,不可知。比拟象征,含蕴深厚,不言别情,而情在其中。未上路,而先想归乡,可见对故乡、亲人、知己的感情之深。这就为下面的行役悲思作了铺垫。
诗的三四两句,叙述别后之悲思。“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这两句是化用古诗 “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句意。暗示悲伤到了极点,只有呜咽吞泣而已。平平地叙事,感情却起了波澜,点出行役之苦,思乡之痛,苦痛交加,自难承受,而产生了悲伤气结不能言的行为。把感情发展到了高潮。仿佛诗意尽于此,把人引入情海之中,玩味、品尝,经历这感情的痛苦历程,这就是诗家所说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
诗的五六两句绝处逢生,宕开一笔,转写未来。“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前途渺茫,心情暗淡,预兆着有故乡不得归的惨极心境。诗至此戛然而止,照应开端,浮云日暮有归宿,而自己的人生归宿,却难以预料,相映相衬,令人生悲。
该词上片写弱柳初秋,一派凄切悲凉之景。下片借柳托恨,抒发无限楼空人去,孤苦无依之感。作者借景抒情,以秋天的萧瑟,表达自己内心的悲凉之感。
上片开始,点名时节,“三眠未歇,乍到秋时节。”时令为初秋时分,一个“乍”字刻画出了秋天的突然而至,为写离别之苦展开铺垫。此处虽然没有写道离别,也没有刻画离别,但却从一个“乍”字,就凸显出了离别的伤感。
“树斜阳蝉更咽,曾绾灞陵离别。”伤感蔓延开来,离别便顺理成章地牵引出来,夕阳西下,在树梢上的太阳,更显得日落西山的迷茫。而后面一句, 则是直接描写柳条变得枯黄,柳叶凋零,柳絮早已化作浮萍随风而逝,秋天真的到来了。“絮已为萍风卷叶,空凄切。”纳兰兀自悲切,感伤这季节的无情和人世间无情的变更。
而到了下片,纳兰却表现出一种温情脉脉的情绪来,他轻柔地写道“长条莫轻折。”不要轻易地折断柳条诉说离别,离别虽有遗憾,但只要不告别,内心便依然充满温情。而后一句“苏小恨,倩他说。”则是在写一代名 妓苏小小。苏小小的爱情故事凄婉动人,离别是这个故事的主题,纳兰用苏小小的典故写出自己的惆怅与伤感,他达到了托物抒怀、借景言情的目的。
而后的两句,自然也是围绕离别而写:“尽飘零游冶章台客。红板桥空,湔裙人去,依旧晓风残月。”词写到这里,颇有几分柳永的风范,但纳兰更显得干脆,既然红桥之上,离别已经无法挽回,那么就干脆道别了吧。就让自己与这晓风残月,独自相守,为离去的人祝福。这首词写出了词人悲凉的心境。
该词咏秋初之柳,作为咏柳之作,纳兰以写景开始,以抒情终结。苍凉的景色中透露内心的悲凉。在万物调零的秋天,词人在一片美景中悲哀地感伤,整首词的情致极为凄婉,是首上乘之作。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