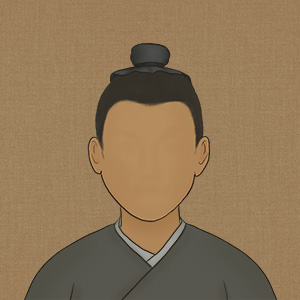《南邻》是用两幅画面组成的一道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前半篇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山庄访隐图。
杜甫到人家作客,诗先写这家人家给予杜甫的印象。诗人首先看到的,主人是位头戴“乌角巾”的山人;进门是个园子,园里种了不少的芋头;栗子也都熟了。说“未全贫”,则这家境况并不富裕。可是从山人和全家的愉快表情中,可以知道他是个安贫乐道之士,很满足于这种朴素的田园生活。说起山人,人们总会联想到隐士的许多怪脾气,但这位山人却不是这样。进了庭院,儿童笑语相迎。原来这家时常有人来往,连孩子们都很好客。阶除上啄未的鸟雀,看人来也不惊飞,因为平时并没有人去惊扰、伤害它们。这气氛是和谐、宁静的。三、四两句是具体的画图,是一幅形神兼备的绝妙的写意画,连主人耿介而不孤僻,诚恳而又热情的性格都给画出来了。
随着时间的推进,下半篇又换了另一幅江村送别图。“白沙”、“翠竹”,明净无尘,在新月掩映下,意境显得特别清幽。这就是这家人家的外景。由于是“江村”,所以河港纵横,“柴门”外便是一条小河。王嗣奭《杜臆》曰:“‘野航’乃乡村过渡小船,所谓‘一苇杭之’者,故‘恰受两三人’”。杜甫在主人的“相送”下登上了这“野航”;来时,他也是从这儿摆渡的。
从“惯看宾客儿童喜”到“相送柴门月色新”,不难想象,主人是殷勤接待,客人是竟日淹留。中间“具鸡黍”、“话桑麻”这类事情,都略而不写。这是诗人的剪裁,也是画家的选景。
这是一首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作两层。前六句为笫一层,写诗人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诗人继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而是余味曲包,耐人寻味。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这两句是说,调转车头我驾着车子开始远行,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到达。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这两句是说,抬头四顾,但见原野茫茫,春风吹拂摇动着原野上无边的青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说,一路上我所见的不再是我认识的旧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岁月催人老。
首起两句叙事,写诗人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还乡省亲,诗人并没有言说。不过结合全诗来说,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事业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全失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应该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自己的故乡。从诗人笔下的描绘来看,此时应该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现在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个诗人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就隐隐地带有沧桑感。紧接着诗人由眼前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一路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不见了,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古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耆老,但见新少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这两句是说,人生和草木的兴盛和衰败都有各自的时限,苦恼的是自己没有很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两句是说,人没有像金石那样坚固,怎么能长寿无尽期?
这两句用来比喻人的生命短暂和短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有一说荣名则谓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认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搏取功名,建树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就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诗人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的事。从全诗来看,诗人还是认真地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美名,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的,并以此自警自励。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百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是一首咏史诗,写刘邦、项羽鸿门之会。此诗前六句,写秦末大乱,楚、汉抗争,作时代氛围的刻画;中间六句,从大形势的渲染跳到宴会上,分别描写刘、项双方:刘邦的志向、实力,项羽的气概、军威;后四句则概括了鸿门会的结局,以刘邦溜回军中,范增撞碎玉斗宣告了鸿门会的结束。全诗结构紧凑,用词精炼,事至繁而笔极简,造语奇崛,意境幽诡。
杨维桢这首诗的所长是想象丰富,运笔兼有空灵和奇崛两个不容易统一在一起的特点。鸿门宴中刘邦、项羽以及范增、项庄、樊哙、张良等都有许多生动的性格鲜明的言语行动,这些经过司马迁的刻画,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若再重复描写,便无新意。如张宪《鸿门会》写:“披帷壮士发指冠,侧盾当筵请公舞。白发老臣心独苦,玉玦三看君不语。”这不如读《史记》更具体、更生动。杨维桢此《鸿门会》则不然,他完全撇开刘、项等人在宴会中具体的言语行动,而驰骋其缥缈不羁的灵思,从当时群雄角逐的大形势着眼,刻画其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时代氛围。因此,读此诗的时候有一种读《史记》时所没有的审美感受。
此诗前六句,纯作时代氛围的刻画。首句迭用两个“迷”字,极言天地混沌莫辨之状,暗喻秦末天下无主,一切都动荡不定的情势。其时秦王子婴已降,秦军已摧垮了,然各起义将领拥军自重,为“东龙”或为“西龙”行云布雨,阴晴不定。一场更为复杂、难以逆料的战争在酝酿着,因为“照天万古无二乌”,天无二日,秦朝一亡,揭竿起义的诸将领终究是要决一雌雄的。鸿门会可以说正是这一矛盾激化与公开化的标志。
中间六句,从大形势的渲染顿然跳到宴会上,分别描写刘、项双方:刘邦的志向、实力,项羽的气概、军威。诗中描写项羽,称他“将军下马力排山”。项羽素以勇猛称,设鸿门宴把刘邦召来,虽然恼恨刘邦捷足先登,然也并没有把刘邦当作一回事,大有一跺足便可使山河颤抖之气概。故诗中以“气卷黄河酒中泻”句形容之。李贺《梦天》诗有“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描写从天上望下来大海之小似乎只能注满一杯;此则写项羽气概之大,似乎可以把黄河注入酒杯中,一饮而尽。此充分说明了项羽对潜在的敌手刘邦是掉以轻心了。
后四句则以极精练、极富韵致的笔调,概括了鸿门会的结局。“剑光上天寒彗残”鸿门会中双方剑拔弩张,最惊心动魄者莫过于项庄舞剑了。诗写其直如天上飞划而过的彗星,是险到了极点。而后,项伯为报张良救命之恩通敌,项羽因自傲而手软,其结果是刘邦得以逃席逸去,鸿门会不了了之,这便是诗中所写的“将军呼龙将客走”的局面。项羽坐失了消灭潜在对手刘邦的最佳时机,对此范增愤愤不已,在刘邦脱身后,张良谢,以白璧一双赠项羽,玉斗一双赠范增。项羽受璧,范增则恼恨已极,置玉斗于地,拔剑撞而破之。诗人高度评价范增的识见,故把他撞玉斗的行动喻为“石破青天”。
全诗造语奇崛,意境幽诡,颇有些接近李贺的风格,个别地方如“碧火吹巢”,袭自李贺的《神弦曲》:“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他没有正面去实写刘、项对峙的军事形势,而是用了一连串似乎无关的奇特的比喻加以烘托。如“东龙白日西龙雨”、“残星破月开天余”、“碧火吹巢”、“石破青天”等词句,均难以通常的语法或逻辑去理解。然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又十分形象地勾画了秦末动乱的社会状态以及波谲云诡的政治、军事的形势。这样一种以许多奇丽古怪的物象来烘托诗歌意旨的手法正是李贺诗歌的特征,显然杨维桢此诗颇多借鉴李贺之处,特别是同一题材的《公莫舞歌》。然比较而言,李贺的《公莫舞歌》稍嫌堆砌,格局不大,此诗则纵横驰骋,元气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