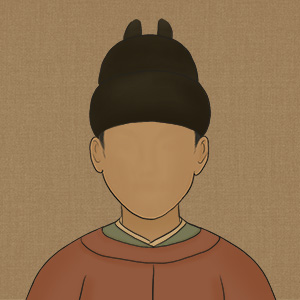这首诗描写一座开满鲜花的江中小岛的美丽景色,却并未正面描绘,而是通过细微的观察、敏锐的嗅觉以及丰富的想象来加以表达,构思甚为奇特,极具艺术效果。
蜂蝶采花,本为自然现象,但这里用“去纷纷”极言其多,且都飞向同一方向,可见某一地方对它们的吸引力之巨大,已暗点“花岛”的存在和魅力。继观察到这一奇特现象之后,诗人顺着蜂蝶飞去的方向,调动嗅觉,顿时感到扑鼻的香气隔着宽阔的江面传送过来,香气隔岸可闻,可见花香之浓郁,而由花香之浓郁,则又不难想见繁花之茂盛。一句视觉,一句嗅觉,虽未直接展示花岛,却已足以撩动读者的向往之情,也足以调动人们的想象力了,亟欲一睹美景的人们自然要争相打听其具体方位。那么,这花岛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诗人给出的答案是“欲知花岛处,水上觅红云”,“水上”是花岛的地理位置,“红云”则是指出了花岛的隐约所在。因为隔着宽阔的江水,无法看清花岛的真面目,只是隐约可见远方似有一片红色的云彩,那就是花岛的具体位置。远望如红云,则近处其花之繁盛可以想见。诗以一句轻松的指点,给读者以启发,从而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想象,诗的意境也就更为深厚。全诗短短二十字,且平白如话,但却包含着曲折的心理过程,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隽永的回味,极见艺术构思的匠心。
顾敻九首《荷叶杯》,很像是写的一个女子的相思全过程。《栩庄漫记》评曰:“顾敻以艳词擅长,有浓有淡,均极形容之妙。其淋漓真率处,前无古人。如《荷叶杯》九首,已为后代曲中一半儿张本。”
这首词写女子的春情。首二句写柳绿花红,正是艳阳好天,女子在赏春。“陌上”二句写她看见了路上有个少年,很逗人爱,她仿佛嗅到了少年身上的香味。后用叠句,表现她的感情在激荡,春情欲狂。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