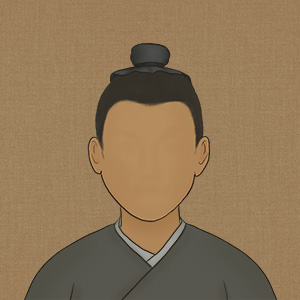空山孤殿在,荒径一僧归。
苔色骄秋雨,松声振夕褷。
惊乌初有托,近亦出林飞。
空山孤殿在,荒径一僧归。
苔色骄秋雨,松声振夕褷。
惊乌初有托,近亦出林飞。
惜春和怜花的情感中,不仅仅是对自然美的珍惜,而且包含着一种自怜、对人生短促的叹惜、对生命不能圆满的茫然。也就是所谓的写景以自况,借花以自怜。《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怜花、葬花最明显也最强烈地表现了这种心态。
这首诗直露惜花之情,并借惜花来表达她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慨和对美的呼唤。前两句写象征邪恶力量的横雨狂风侵袭着象征美好事物的花;后两句写呼唤青帝为落花做主,莫让风雨欺凌花,隐含着诗人对人间幸福和美的呼唤。诗写得含蓄而深情。
唐代的孟浩然曾写过一首有名的“惜花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人在春眠中被欢快的鸟啼惊醒,想来当时还并未完全从梦中清醒,却唯独想起了昨夜的风雨和遭风雨的花。怜花之情写得很是生动。而这首朱淑真的诗,惜花之情却写得更是直露。
起首两句,展开的似乎是一种搏斗的场面,一方面是正在开的弱花,另一方则是满怀妒意的横雨狂风,作者用“正”和“便”两个字突出了其间时间的紧迫,有搏击的紧张感。“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花开正好,风雨何急,但是在作者眼里,横雨狂风夹着妒意向落花袭来时,已经成为人间暴虐力量的化身,而那正当新鲜、美好而又娇嫩的花枝则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作者眼中不仅仅只有落花,还有落花般不幸的人生、世事:人之无力掌握捉弄人的命运,而人间暴虐的力量往往占上风。这两句实际上是对人世生活的一种概括。
诗人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和苦难重重的人生,只能从内心发出呼唤:“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在乞求司春之神保护花儿,不要落下地成为尘埃的心情中,实际上隐含着诗人对人间幸福和美的呼唤。这种呼唤有点类似于晚清诗人龚自珍写“我劝天公重抖擞”时的浪漫精神。整首诗的情花之情,并非是对自然景物的感慨,而是对人生的感溉,诗表达的主要是一种哲理,以落花来写人世的风雨沧桑,以惜花来表达她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慨和对美的呼唤。
将这首诗与孟浩然的那首诗作以比较,孟诗的意象和情感更自然,更生动,形象和意念结合得更紧密,更饱满,而这首诗则理大于象,理大于情,如果说孟诗更合于林黛玉所说的:“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里就到那里”,那么朱淑贞的诗则是为理而作的诗。这也是唐诗与宋诗的基本区别。
此诗前八句乃幻想之辞,写天上情景,似与诗之主旨无关。汉乐府多用于宴间演奏,取悦宾客,颇有拼凑割裂现象。此数句又见于《步出夏门行》末段。但乐工拼凑之时,应不会毫无理由,信手胡来。张玉谷谓"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唯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子,自出待客不得已来"(《古诗赏析》),并指出其于后面写"健妇"一段有互相映衬发明之作用,"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相关"(同上)。即可备一说。也有人认为此段是乐曲之"艳词"(前奏),亦属可能。诗描写"健妇",取材于一次她接待宾客的全过程:"迎客"、"问客",热情有礼;"请客"、"坐客",殷勤周到;然后酌酒与客、促令办饭等种种描述,不厌其烦:无一不反映出她举止得体,善主中馈。诗中之"客",恐怕不是一般的亲友作客者,而是来自中原之过客,故有送客"废礼"之疑惑, "齐姜不如"之赞美。此诗写女子而忽略其容貌体态,专一述其"健"(才干),可谓别具只眼,亦可见西北地区之民俗。描述看似琐屑,然笔笔紧扣"健"字刻绘,因而人物形象,益见鲜明。
前八句写天上景物。若理解这几句,须先阐明其隐喻之义。“白榆”指玉衡星。“桂树”指桂星。纬书说“椒、桂生合刚阳。”注文说:“椒桂,阳星之精所生。”道,黄道。《汉书·天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是想象中的太阳轨道。青龙,东方七宿总名。凤凰即鹑火。纬书《春秋元命包》说:“火离为凤凰。”《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说:“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星也。”(案闻一多说:尾本东官宿,当为龙尾。此云凤将九雏盖与南宫朱雀相乱。)
这八句在表现上,颇有特点。其一,因名借物,赋以形态。某些星宿本以动、植物命名,诗人信手拈来,将它们化为动、植物物本身的形象;并且借“黄道”为通衢大道(古有所谓“天衢”的说法),将这些动、植物形象井然有序地系列在“大道”两旁,于是造成一种迥异于人间的“仙境”。诗人借物赋形是有选择的。“桂树”令人想到传说中的“月桂”,“龙”、“凤”是传说中天上的灵物。就是“白榆”也同寻常人间的榆柳不同。这些事物都是烘托“仙境”所不可少的。其二,这种神仙境界出于诗人的想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其中的一事一物都实有所指,犹如打灯谜,其用意不在字面,可谓之虚而能实。其三是想象奇妙。全部诗意都是从想象生发出来。否则,几个星宿的名称是构不成诗意的。这八句诗用的是诙谐风趣的笔调,所以虽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却并非在着意写神仙事。这种将星宿经作动、植物和人作为诗的意象的写法,《陇西行》之前就有,象《小雅》的《大东》篇和《九歌》的《东君》。尽管《东群》写得颇为壮美,却也不还不能象本篇一样创造出完整意境。
“好妇出迎客”以下二十四句颂美一位能独特门户的“健妇”,是《陇西行》歌辞的正题。诗因何而作,本事已无可稽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引《乐府解题》说:“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这也只是就字面说的。
写法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用笔工细。譬如写主人待客一节,先写“请客北堂上”指明客座应安设的方位,继写“坐客毡氍毹”,表示对客人的恭敬,其中也包含待客的规格。摆酒要摆出“清”“白”两样,虽说不上是丰盛,却是在避免单调,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周到。所有这些,都很能表现主人公的讲究礼数。有几个细节写得非常妙。如写主人公迎客时,说“伸腰再拜跪”,写在酒席前应酬,说“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全是连续动作;这类句子,用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曲尽其态。又如写主人用好酒待客,说“酒上正华疏”。倒在杯子里的酒涌出水平面形成一条条的花纹,正表明酒好。这种写法,应当说是比较形象比。象这样绘形绘色的笔墨,在乐府诗中是并不多见的。
第二是叙事的严整有序。开首二句“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简炼地画出主人公的容貌姿态。接着写她对客人施礼、寒暄,把客人让进堂屋,再写为客设座,再写摆酒陪客,再写酒罢备饭,最后送客尽礼,显得有极有章法。这样写,同诗中表现主人公的落落大方,处事的稳健练达是一致的。
第三是文字质朴。质朴是乐府叙事篇章的共同特点,而本篇尤为突出,描叙一事一物,莫不从实处着笔;并且做到朴素而能生动传神。如“左顾”、“敕”、“促令”、“盈盈”、“趋”等字眼,都极富表现力。
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诗人由衷赞美说,古代的贤妇人齐姜同她相比也不免逊色,说她是胜过“丈夫”的“健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赞誉,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也正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中出格的地方。但诗中写她所有的行为都不仅没有超越,而且是严格遵循封建礼法的。这一点,则是主人公性格的核心。诗的写法,从始至终扣在一个“礼”字上。
这首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前两句写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后两句想象魏二梦里听见猿啼,难以入眠。诗歌表面写好友分别后愁绪满怀,实际上是写作者送别魏二时感叹唏嘘的情感。全诗虚实结合,借助想象,拓展了表现空间,扩大了意境,深化了主题,有朦胧之美,在艺术构思上颇具特色。
首句“醉别江楼橘柚香”是点明送别魏二的饯宴设在靠江的高楼上,空中飘散着橘柚的香气,环境幽雅,气氛温馨。这一切因为朋友即将分手而变得尤为美好。这里叙事写景已暗挑依依惜别之情。“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贾至《送李侍郎赴常州》),首句“醉”字,暗示着“酒深情亦深”。
寒雨连江”则是表明气候已变。次句字面上只说风雨入舟,却兼写出行人入舟;诗中不仅写了江雨入舟,然而“凉”字却明白的表现出登舟送客的惜别场景来,“凉”字既是身体上的感触,更暗含诗人心中对友人的不舍和对离别的伤怀。“引”字与“入”字呼应,有不疾不徐,飒然而至之感,善状秋风秋雨特点。此句寓情于景,句法字法运用皆妙,耐人涵咏。凄凄风雨烘托诗人惜别知音,借酒消愁的悲凉心情。
三四句“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以“忆”字勾勒,从对面生情,为行人虚构了一个境界:在不久的将来,朋友夜泊在潇湘之上,那时风散雨收,一轮孤月高照,环境如此凄清,行人恐难成眠吧。即使他暂时入梦,两岸猿啼也会一声一声闯入梦境,令他睡不安恬,因而在梦中也摆不脱愁绪。诗人从视(月光)听(猿声)两个方面刻画出一个典型的旅夜孤寂的环境。月夜泊舟已是幻景,梦中听猿,更是幻中有幻。所以诗境颇具几分朦胧之美,有助于表现惆怅别情。
末句的“长”字状猿声相当形象,有《水经注·三峡》中描写猿声的意境:“时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长”字作韵脚用在此诗之末,更有余韵不绝之感。
此曲以“晚秋”作题,描写送别时的伤感。晚秋本身有一种凄凉萧瑟的气氛,更加快衬出伤感离别之痛,反映出作者与洛神失之交臂的无限痛苦。
运用典故闪示意象而不加详述,从而启动读者的经验和联想,是古代文学作品常用的表意手法。文章开头连用陈王罗袜、学士琵琶两个典故,开篇点题。接着又用“泪酒”和“秋花”两个意象,来加强文章的伤情色彩。面对漂泊天涯的处境,只能酒泪齐下,有着无限的哀思。挥手自此去,天涯两地人,加上作品中着意突出深秋的肃杀,收到令人了黯然神伤的效果。
从曲子起首两句的两则典故来看,内容都同异性之间的萍水相逢有关,这种邂逅引出了一段动情的故事,然而其悲剧性正在于情缘的昙花一现。诗人已明知“梦断”,却依然禁不住“情伤”,可见他的一往情深,这种注定无法再现的情梦,便为全曲定下了一种惆怅与失落的基调。值得一提的是,曹植的《洛神赋》记称“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虽未说明具体的时日,但赋中有“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语,可知他与洛神的相遇正值秋季;而白居易《琵琶行》,则明言“枫叶荻花秋瑟瑟”、“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两个典故都符合“晚秋”的题面,在本作中恐怕不是偶然的。这样一来,“又见西风换年华”,既是作者的真切感受,又与前述的典故照应相合,就更觉意味深长了。
在秋天的悲凉气氛中,作者又以苦酒与残花为陪衬,叙出了自己“天一涯”的漂泊现实。一场情梦本就无凭,再加上时间的暌隔(“又见西风换年华”)与空间的距离(“行人天一涯”),就使人倍觉不堪了。作品的每一句都不啻为一声叹喟,诗人将这种种内容纳于“晚秋”的题目之下,其处境与心境的悲凄,就是呼之欲出的了。
此曲的主要艺术特色是大量引用前人离别伤感的诗句,来表现作者的离愁别绪,堪称一首写离别的佳作。文章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全文写离别却无一“离”字,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