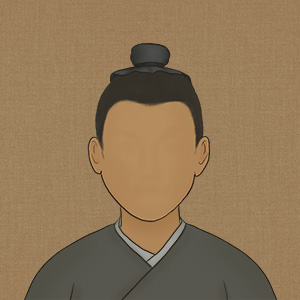这首诗创作于作者得知白居易遭贬之后。此诗以景衬情,以景写情,叙事抒情,表现作者对白居易的一片殷殷之情。首句描写了自己所处之阴暗的背景,衬托出被贬谪又处于病中的作者心境的凄凉和痛苦;次句点明题意;第三句写当听说白居易被贬的消息时的情景,表现了诸多的意味;末句,凄凉的景色与凄凉的心境融恰为一,情调悲怆。全诗表达了作者知道好友被贬后极度震惊和心中的悲凉。
元稹贬谪他乡,又身患重病,心境本来就不佳。此时忽然听到挚友也蒙冤被贬,内心更是极度震惊,万般怨苦,满腹愁思一齐涌上心头。以这种悲凉的心境观景,一切景物也都变得阴沉昏暗了。于是,看到“灯”,觉得是失去光焰的“残灯”;连灯的阴影,也变成了“幢幢”——昏暗的摇曳不定的样子。“风”,本来是无所谓明暗的,而今却成了“暗风”。“窗”,本来无所谓寒热的,而今也成了“寒窗”。只因有了情的移入,情的照射,情的渗透,连风、雨、灯、窗都变得又“残”又“暗”又“寒”了。“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入寒窗”两句,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是以哀景抒哀情,情与景融会一体、“妙合无垠”。
诗中“垂死病中惊坐起”一语,是传神之笔。白居易曾写有两句诗:“枕上忽惊起,颠倒着衣裳”,这是白居易在元稹初遭贬谪、前往江陵上任时写的,表现了他听到送信人敲门,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元稹来信的情状,十分传神。元稹此句也是如此。其中的“惊”,写出了“情”──当时震惊的感情;其中的“坐起”,则写出了“状”──当时震惊的模样。如果只写“情”不写“状”,不是“惊坐起”而是“吃一惊”,那恐怕就神气索然了。而“惊坐起”三字,正是惟妙惟肖地摹写出作者当时陡然一惊的神态。再加上“垂死病中”,进一步加强了感情的深度,使诗句也更加传神。既曰“垂死病中”,那么,“坐起”自然是很困难的。然而,作者却惊得“坐起”了,这样表明:震惊之巨,无异针刺;休戚相关,感同身受。元、白二人友谊之深,于此清晰可见。
此诗的中间两句是叙事言情,表现了作者在乍一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的陡然一惊,语言朴实而感情强烈。诗的首尾两句是写景,形象地描绘了周围景物的暗淡凄凉,感情浓郁而深厚。
按照常规,在“垂死病中惊坐起”这句诗后,大概要来一句实写,表现“惊”的具体内涵。然而作者却偏偏来了个写景的诗句:“暗风吹雨入寒窗”。这样,“惊”的具体内涵就蕴含于景语之中,成为深藏不露、含蓄不尽的了。作者对白氏被贬一事究竟是惋惜,是愤懑,还是悲痛,全都没有说破,全都留给读者去领悟、想象和玩味了。
元稹这首诗所写的,只是听说好友被贬而陡然一惊的片刻,这无疑是一个“有包孕的片刻”,也就是说,是有千言万语和多种情绪涌上心头的片刻,是有巨大的蓄积和容量的片刻。作者写了这个“惊”的片刻而又对“惊”的内蕴不予点破,这就使全诗含蓄蕴藉,情深意浓,诗味隽永,耐人咀嚼。
这首诗用简练生动的语言,通过“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等一系列的凄凉景象的描写和气氛的烘托,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好友被贬的哀伤不平和凄苦的心情。白居易在江 州读诗后,深受感动。后来在《与元微之书》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日本明治维新前夕,诗僧月性在离乡东游前写了两首自述其志向的题壁诗《锵东游题壁二首》。后来被西乡隆盛读到了,他认为其中第二首诗的内容符合自己的抱负,便稍作修改后存留着自勉。清朝末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国将不国、 民不聊生。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成为中国有志青年效法的榜样,西乡隆盛的著名事迹也流传到了中国。
由此可以推断:在这种条件下,少年毛泽东或者是从书籍报刊上,或者是直接从留学东洋的教师那里,读到了西乡隆盛版本的这首述志诗。之后,他坚持要离家前往湘乡接受更加高等的教育,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与固执守旧的父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他改动了这首诗的几个字,而后呈给父亲。
首诗是少年毛泽东走出乡关、奔向外面世界的宣言书,从中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这是一首典型的言志诗。
起首两句所表述的诗意,思想鲜明、气势雄伟、铿锵有力。“立志出乡关'’的毛泽东,用“学不成名誓不还”的绝唱,表明了他求学的坚决、志向的高远。
后两句将上述诗意向更深的意境进行挖掘,动用先否定、后肯定的手法,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死后尸骨何必非要归故里,人生行至何地自有青山随的诗意。从诗句中,自然而然地发出寓意深远的感叹,从而受到启迪。
全诗通俗易懂,平仄押韵流畅,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巧借古今中外经典词句,变为自己明志之诗句,简洁而不简单,通俗不失大雅,是毛泽东心态、 志向的真实流露。一个胸怀不凡志向,聪慧、 倔强、 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顽强毅力的毛泽东,正迈向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